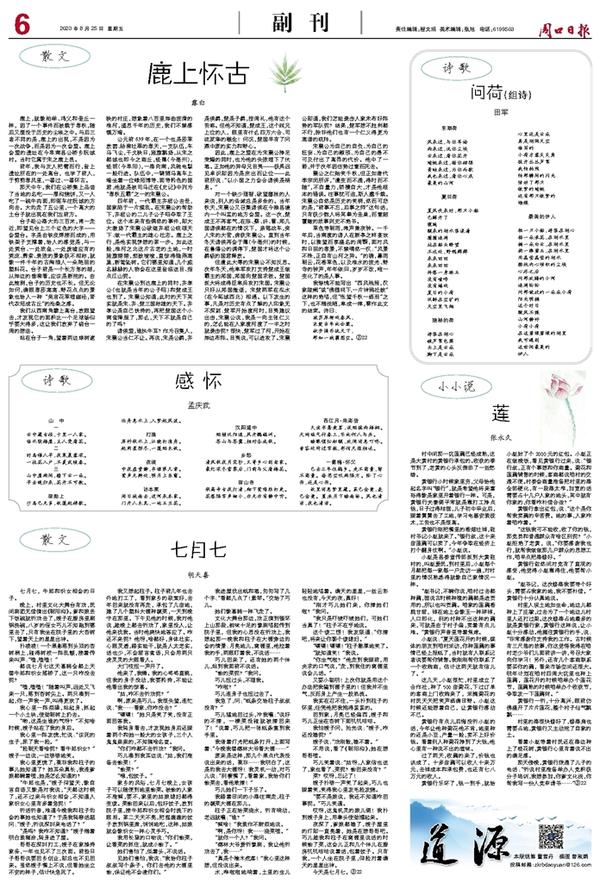鹿上,就像柏举、鸡父和壶丘一样,因了一个事件而被载于春秋,随后又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与后三者不同的是,鹿上的出现,不是因为一次战争,而是因为一次会盟。鹿上会盟的遗址在今阜南县公桥乡阮城村。当时它属于宋之鹿上邑。
前年,我与友人把臂而行,登上遗址所在的一处高台,也学了前人,于剪剪春风里,一番过、一番怀古。
那天中午,我们在公桥集上品尝了当地的名吃——展沟烧饼,又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即驱车往阮城的方向去。大约走了五公里,一个高大的土台子就出现在我们左前方。
台子距公路大约三百米,甫一走近,即望见台上三个红色的大字——会盟台。字是由铁皮焊接而成的,用铁架子支撑着,给人的感觉是,与一处荒台、一处故垒、一处废墟应有的荒凉、萧索、衰败的景象极不相称,就像一件千年的古陶插入一朵艳丽的塑料花。台子前是一个长方形的湖,从岸边的垂柳看,应该是新挖的。由此推测,台子的历史也不长。但无论如何,满眼春莎离离、野花点点的景象也给人一种“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沧桑之感。
我们从西南角攀上高台,放眼望去,才发现它的面积比一个足球场似乎要大得多,这让我们放弃了绕台一周的想法。
站在台子一角,望着两边绿树遮映的村庄,想象着八百里岸曲波清的淮河,遥思千年的历史,我们不禁感慨万端。
公元前639年,在一个也是莎草放茵、杨柳吐翠的春天,一支队伍,车马飞尘,干戈映日,旌旗飘扬,从宋之都城也即今之商丘,经薄(今亳州),经胡(今阜阳),一路向南,风驰电掣一般行进。队伍中,一辆驷马高车上端坐着一位峨冠博带、面带矜色的国君,他就是被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
四年前,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国家陷于一片混乱。在宋襄公的帮助下,齐桓公的二儿子公子昭夺取了王位。这个本来有些偶然的事件,却大大激扬了宋襄公欲继齐桓公统领天下、做一代霸主的雄心壮志。鹿上之行,是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如此这般,淮河之北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时旌旗猎猎,笳鼓喧喧,直惊得雏燕离巢,新莺坠树。它们哪里知道,几个威名赫赫的人物会在这里登临送目、指点江山呢。
在宋襄公到达鹿上的同时,齐孝公(也就是当年的公子昭)和楚成王也到了。宋襄公知道,此时的天下其实就是宋、齐、楚三国称雄的天下。齐孝公是自己扶持的,再把楚国这个小南蛮降服了,那么,天下不就是自己的了吗?
诸侯盟,谁执牛耳?作为召集人,宋襄公当仁不让。再说,宋是公爵,齐是侯爵,楚是子爵,按周礼,他有这个资格。但他不知道,楚成王,这个弑兄上位的人,眼里有什么四方六合、司徒冢宰的概念!何况,楚国早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和野心。
因此,鹿上之盟在为宋襄公挣足荣耀的同时,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正如他的异母兄目夷——极具远见卓识却因为是庶出而让位——此前所说:“以小国之力会合诸侯是祸患。”
对一个缺少理智、欲望膨胀的人来说,别人的告诫总是多余的。当年秋天,宋襄公又召集诸侯在今睢县境内一个叫盂的地方会盟。这一次,楚成王不再客气,在陈、蔡、许、曹、郑几国诸侯都在的情况下,亲驾战车,突入宋的大营,虏获宋襄公。直到当年冬天诸侯再会于薄(今亳州)的时候,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国才将这个公爵级的国君释放。
但遭此大辱的宋襄公不知反思。次年冬天,他率军攻打支持楚成王做霸主的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宋国。宋襄公只好从郑国撤退,宋楚两军在泓水(在今柘城西北)相遇。以下发生的事,凡是对历史有点了解的人印象无不深刻:楚军开始渡河时,目夷建议出击,宋襄公说,我是一向主张仁义的,怎么能在人家渡河渡了一半之时就袭击呢?很快,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说,可以进攻了。宋襄公却道,我们怎能袭击人家未布好阵势的军队呢?结果,楚军想不胜利都不行,除非他们也有一个仁义得更为离谱的统帅。
宋襄公为自己的自负、为自己的狂妄、为自己的颟顸、为自己的愚不可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中了一箭,并于次年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襄公之仁贻笑千秋,但正如唐代李宗闵所评,“遭变而不通,得时而不随”,不自量力,骄横自大,才是他根本的错误。往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宋襄公自然是历史的笑柄,然而可悲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只有极少数人将其奉为圭臬,而重蹈覆辙的故事则史不绝书。
草色带朝雨,滩声兼夜钟。一千年后,当南渡的诸人在新亭之畔宴饮时,以雅望而享盛名的周顗,面对风和日丽的春景,不禁喟然一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确,暮雨朝云,花香草色,以及淮水的波光、野寺的钟声,年年依旧,岁岁不改,唯一变化了的是人事。
我惭愧不能写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这样的绝唱,但“怅望千秋一洒泪”之下,也不揣浅陋,率成一律,聊作此文的结束。诗曰:
坡莎岸柳戏春风,
宋楚当年此会盟。
欲步强齐统天下,
那知一战霸图空。③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