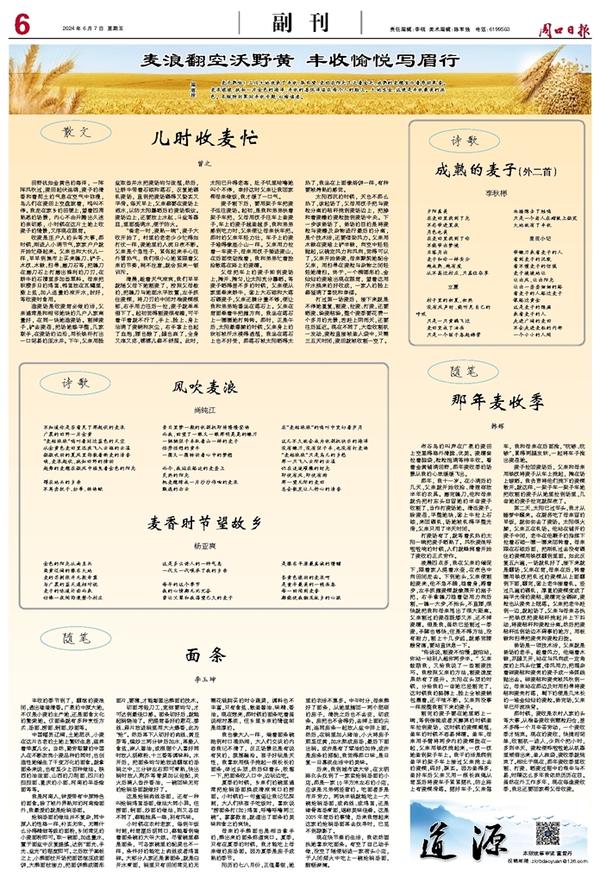编者按
麦子熟啦!三川大地迎来了丰收,举目望,麦田在阳光下泛着金光,成熟的麦穗宣示着劳动果香。麦浪滚滚,犹如一片金色的海洋,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地生金,这便是丰收最美的底色。本版特别策划丰收专题,以飨读者。
(散 文)
儿时收麦忙
曾之
田野犹如金黄色的海洋,一阵阵风吹过,麦田起伏连绵,麦子的清香和着泥土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鸟儿们在麦田上空盘旋着,鸣叫不停。我走在家乡的田埂上,望着四周熟悉的场景,内心不由升腾出久违的亲切感,小时候在这片土地上收麦子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收麦是庄户人的头等大事,那时候,刚进入小满节气,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起来。父亲也和大伙儿一样,早早到集市上买来镰刀、铲子、木杈、木锨、扫帚、磨刀石等,把镰刀在磨刀石上打磨出锋利的刀刃,在耕牛的石槽里多加些草料。母亲把积攒多日的鸡蛋、鸭蛋放在瓦罐里,撒上盐,加入适量的凉开水,封好,等收麦时食用。
造麦场是收麦前必做的活,父亲通常是和相邻地块的几户人家商量好,在同一块地造麦场。割掉麦子,铲去麦茬,把场地修平整,几家联手,在麦场的边沿,用长铁杆打出一口简易的压水井。下午,父亲用脸盆取些井水把麦场均匀泼湿,然后,让耕牛带着石磙和落石,反复地碾轧麦场,直到把麦场碾得又瓷实又平滑。每天早上,父亲都要在麦场上洒水,以防太阳暴晒后的麦场裂纹。麦场边上,还要放上水缸、斗盆等器皿,里面盛满水,便于防火。
“蚕老一时,麦熟一晌”,麦子大收开始了,村里的老老少少忙得如打仗一样,麦地里的人流日夜不断。父亲是个急性子,紧张起来手心往外冒热气,我们很小心地紧跟着父亲的节奏,稍不注意,就会招来一顿训斥。
清晨,趁着天气凉爽,我们早早就随父母下地割麦了,按照父母教的,把镰刀与地面水平放置,左手抓住麦棵,将刀刃的中间对准麦棵根部,右手用力往后一拉,麦子就乖乖倒下了。起初觉得割麦很有趣,可干着干着就不行了,手上、脸上、身上沾满了麦锈和灰尘,右手掌上也起了血泡,腰也酸了,腿也麻了,全身又痒又疼,哪哪儿都不舒服。此时,太阳已升得老高,肚子叽里咕噜地叫个不停,幸好这时父亲让我回家帮母亲做饭,我才缓了一口气。
麦子割下后,要用架子车把麦子运往麦场。起初,是我和弟弟扶着架子车把,父母用杈子往车上装麦子,车上的麦子越装越多,我和弟弟感到吃力时,父亲便让母亲扶车把。那时的父亲年轻力壮,车子上的麦子堆得像座小山一样。父亲用力拉着一车麦子,母亲用杈子插进麦山,在后面使劲推着,我和弟弟忙着捡拾散落在路上的麦穗。
父母把车上的麦子卸到麦场上,摊开、摊匀,让太阳充分暴晒。等麦子晒得差不多的时候,父亲便从家里牵来耕牛,套上大石磙和大落石碾麦子,父亲还嫌分量不够,便让我和弟弟轮番坐在落石上。父亲在前面牵着牛把握方向,我坐在落石上一圈圈地打转转。那时,正是午后,太阳最毒辣的时候,父亲身上的坎衫被汗水浸得透湿,我坐在落石上也不好受,那落石被太阳晒得太热了,我坐在上面像烙饼一样,有种要被烤熟的感觉。
太阳西沉的时候,天也不那么热了,该起场了,父母用杈子把与麦粒分离的秸秆挑到麦场边上,把掺和着麦糠的麦粒拢到麦场中央。下一步该扬场了,扬场的目的是将麦粒与麦糠及杂物进行最后的分离,是个技术活,还要借助风力。父亲用木锨在麦堆上铲半锨,向空中轻轻抛起,以确定风力和风向,觉得可以了,父亲开始扬麦,母亲默契地配合父亲,用扫帚在麦粒与杂物之间轻轻地清扫。终于,一个椭圆形的、金灿灿的麦堆出现在眼前,望着这用汗水换来的好收成,一家人的脸上都溢满了喜悦和幸福。
打过第一场麦后,接下来就是不停地重复,割麦、拉麦、打麦,还要晒麦、垛麦秸垛,整个麦季要花费一个多月的光景,若赶上阴雨天,还要往后延迟。现在不同了,大型收割机一发动,麦粒直接被装入袋中,只需三五天时间,麦田就被收割一空了。
(诗 歌)
成熟的麦子(外二首)
李秋彬
夕阳真美
在麦田里找到了光
不忍带进黑夜
月色也美
在麦田里找到了你
不能带出梦境
日落月出
麦子和你一样安分
越成熟,越有度
从不高过村庄,只盖住杂草
立夏
村子里的初夏,初热
没有风声时,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只是一只黄鹂飞过
麦田变成了油画
只是一个孩子卷起裤管
池塘隐去了蛙鸣
只是一个老人在褶皱上微笑
大地就有了丰收
麦田小记
带镰刀来看麦子的人
看到麦子的沉默
看不懂麦子的惊慌
麦子缓缓地让
让出风,让出阳光
让出一垄垄细细的路
看麦子的人路过麦子
像路过黄金
这是麦子的隐痛
来看麦子的人
走进广阔的麦田
不会走进麦粒的内部
一个小小的人间
(诗 歌)
风吹麦浪
尚纯江
不知道你是否看见了那起伏的麦浪
广袤的田野一片金黄
“麦秸垛垛”鸣叫着划过蓝色的天空
从金黄色麦田里迅疾飞入云端的云雀
微微吹动的夏风里弥散着新麦的清香
哦,麦浪起伏,犹如田野的律动
起舞的麦穗在微风中摇曳着金色的阳光
蹲在地头的乡亲
不再卖杈子、扫帚、扬场锨
昔日里梦一般的收割机即将隆隆登场
而我,回望了一眼又一眼那明晃晃的镰刀
一辆辆架子车驮着山一样的麦子
任劳任怨的黄牛
一圈又一圈转动着心中的梦想
而今,我站在路边的麦垄上
炙热的阳光
把麦穗烤成一片沙沙作响的麦浪
飘逸的白云
在“麦秸垛垛”的鸣叫中变幻着岁月
这儿不久就会成为收割机快乐的海洋
没有镰刀,没有架子车,也没有打麦场
“麦秸垛垛”只是鸟儿的乡愁
那一只飞入云际的云雀
仍在追逐璀璨的时光
即使有风,即使有雨
那一望无际的麦田
总会散发让人舒心的清香
麦香时节望故乡
杨亚爽
金色的阳光从南至北
染黄辽阔的豫东大地
麦的芒刺张开无数希冀
与广袤的蓝天遥相对视
麦子的味道扑面而来
仿佛一夜间弥漫整个村庄
这是多么诱人的一种气息
一代又一代喂养了我的乡亲
每年的这个季节
我的心情都无比亢奋
曾让父辈和我渴望已久的麦子
是豫东平原最真诚的馈赠
杏黄色滚动的麦浪呵
是童年最美的一帧画卷
每一回闻到麦香
都能使我触及故乡的心跳
(随 笔)
面条
李玉坤
丰收的季节到了,翻滚的麦浪间,透出缕缕清香。广袤的中原大地,不仅是小麦的主产地,还是面食文化的繁荣地。仅面条就有多种烹饪方式:汤面、捞面、焖面、炒面等。
中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小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滋养着华夏儿女。当然,勤劳聪慧的中国人在不断改良小麦品种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催生了千变万化的面食。就拿面条来说,也有至少上百种做法。陕西的油泼面、山西的刀削面、四川的担担面、重庆的小面、河南的羊汤烩面等等。
我是河南人,钟爱带有中原特色的面食。除了被外界熟知的河南烩面外,我最爱的就是炝锅汤面。
炝锅汤面的做法并不复杂,同中原人的性格一样,朴实无华。无需什么分得精细等级的面粉,乡间常见的小麦面粉即可。取一碗面,加适量水,置于面盆中反复搓揉,达到“面光、手光、盆光”的程度即可。之后放于案板之上,小擀面杖开场把面团滚压成面饼,大擀面杖接力,把面饼擀成圆形面片,要薄,才能彰显出擀面的技术。
切面考验刀工,宽细要均匀,才可达到最佳口感。面条切好后,就能起锅烧油了。把提前备好的葱花、姜丝、蒜片放进锅里用大火爆香,此为“炝”。然后再下入切好的肉丝、黄豆芽等,煸炒三两分钟后加水,再撒入食盐,淋入酱油,或根据个人喜好同时放入胡椒粉、十三香等调味料。水开后,把面条均匀地放进翻滚的汤锅之中,三分钟左右即可煮熟,快出锅时放入荆芥等青菜加以佐配,关火后滴入些许香油,一碗回味无穷的炝锅汤面就做好了。
这是炝锅肉丝汤面,还有一种叫炝锅鸡蛋汤面,做法大同小异。但捞面、焖面、炒面的做法,则又各自不同了,都能独具一格,别有风味。
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每到午饭时刻,村前屋后胡同口,都能看到端着面条碗的大爷大娘。尽管碗里都是面条,可各家碗里的配菜也不一样,条件好的能吃上肉丝或者鸡蛋碎。大部分人家还是素面条,就是白开水煮面,锅里只有田间常见的无需花钱购买的时令蔬菜,调料也不丰富,只有食盐、散装酱油、味精、香油。现在想来,那时候的面条吃着虽说相对寡淡,但乡里乡亲的情谊却是浓厚的。
我也像大人一样,端着面条碗跑到村口凑热闹,大人们交谈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反正场景总是有说有笑的,氛围融洽。孩子好玩是天性,我喜欢用筷子挑起一根长长的面条,举过头顶,然后仰着头,吸溜一下,把面条收入口中,边玩边吃。
夏季的时候,乡亲们的碗里通常把炝锅汤面换成清凉爽口的捞面。小时候的一句童谣让我记忆深刻,大人们哄孩子吃饭时,喜欢说“捞面条打(加)鸡蛋,呼噜呼噜两三碗”。寥寥数言,就道出了面条的美味和食之的爽快。
母亲的手擀面也是相当拿手的,擀出来的面条筋道爽口。夏季,只有在夏季的时候,我才能吃上母亲做的茄汤面。因为夏季是茄子成熟的季节。
阳历的七八月份,正值暑假,地里的农活不算多。中午时分,母亲擀好了面条,从地里摘回一两个肥硕的茄子,清洗之后也不去皮,切成条。茄把也不舍得扔,去掉上面的尖刺,连同茄条一起放入盆中拌上面。然后,在锅里加入猪油,小火将茄子煎至泛黄,加水熬成茄汤,最后下面出锅。或许是有了荤油的加持,或许是茄条的搭配,我觉得那口味,是日复一日寡淡生活中的美味。
后来,我到城市读大学,在文明路北头找到了一家卖炝锅汤面的小店。那是一家10平方米左右的小店,应该是兄弟俩经营的。吃面者多是市井劳力,两块半钱就能吃上一大碗炝锅汤面,或肉丝、或鸡蛋,还是猪骨高汤煮面,堪称美味佳肴。这是2005年前后的事情,后来我想起来这家的炝锅汤面再去找寻时,已觅不到踪影了。
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我依然固执地喜欢吃面条。有空了自己动手做,没空了随便钻进一家街头小店,于人间烟火中吃上一碗炝锅汤面,酣畅淋漓。
(随 笔)
那年麦收季
韩辉
布谷鸟的叫声在广袤的麦田上空显得格外清脆、优美。麦穗耷拉着脑袋,粒粒饱满等待丰收。看着金黄铺满田野,那年麦收季的场景从我的心底缓缓飞出。
那年,我十一岁。在小满后的几天,父亲就开始收拾、清理存放半年的农具。磨完镰刀,他和母亲就先把村东头自留地的半亩麦子收割了,当作打麦场地。清运麦子,除麦茬,平整地块,套上牛拉上石磙,来回碾轧,场地被轧得平整光滑,父亲只用了半天时间。
打麦场有了,就等着炙热的太阳一晌把麦子晒熟了。风吹麦浪呼啦啦响的时候,人们就蜂拥着开始了麦收的正式劳作。
凌晨四点多,我在父亲的催促下,跟着家人提着水壶,在夜色中向田间走去。下到地头,父亲便割起麦来,他不急不躁,稳着身,跨着步,左手抓握麦棵就像展开的扇子把,右手拿镰刀稳着劲用力向后割,一镰一大步,不抬头,不直腰,很快就把我和母亲甩出了很大距离。父亲割过的麦茬既矮又齐,还不掉麦穗。倒是我,虽然已经割过一季麦,手脚也够快,但是不得方法,没有耐力,割上十几步远,就感觉腰酸背痛,要站直休息一下。
“俗话说,割麦不怕慢,就怕站,你站一站别人超你两步半。”父亲鼓励我,又给我说了一些割麦技巧。我按照父亲的方法,割麦速度果然有了提升。太阳在头顶的时候,分给我的一亩地已经割完了,这时候我的胳膊上、脸上全被麦锈包裹着,还干咳不断。父亲则没事一样规整我割下来的麦子。
割完的麦子要在地里晒上一晌,等到傍晚或者天擦黑的时候装车拉到麦场,这时候的麦棵潮湿,装车的时候不容易掉穗。装车,母亲用手臂将两步内的麦棵拢在一起,父亲用铁杈挑起来,一杈一杈地装到架子车上。我干的活是爬到装平的架子车上接过父亲挑上去的麦棵,码好,踩实。因为装得多,装好车后父亲又用一根长麻绳从前至后将麦车子紧紧捆扎,防止路上有麦棵滑落。捆好车子,父亲驾车,我和母亲在后面推,“吭哧、吭哧”,累得两腿发软,一起将车子推出麦茬地。
麦子拉回麦场后,父亲和母亲用铁杈将麦子从车上挑起,摊在场上晾晒。我负责将他们挑下的麦棵散开。就这样,一架子车一架子车地把收割的麦子从地里拉到场里,几亩地的麦子拉完就深夜了。
第二天,太阳已过竿头,我才从睡梦中醒来。在厨房吃了母亲留的早饭,就匆匆去了麦场。太阳很火辣,父亲正在轧场。他站在铺开的麦子中间,老牛在他鞭子的指挥下拉着石磙一圈一圈来回转着。母亲跟在石磙后面,把刚轧过去没有碾住的麦棵用铁杈翻到里面。如此反复五六遍,一场就轧好了。接下来就是翻场,父亲在前,母亲在后,转着圈用铁杈把轧过的麦棵从上面翻到下面,翻完,套上老牛接着轧。经过几遍的碾轧,厚重的麦棵变成了扁平光滑的麦秸,麦穗完全碾碎,麦粒也从麦壳上脱落。父亲把老牛赶到一边,就起场了。父亲与母亲各执一把铁杈把麦秸秆挑起并上下抖动,将麦秸秆和麦粒分离。然后把麦秸秆运到场边不碍事的地方,用板锨和扫帚把麦壳和麦粒归拢。
扬场是一项技术活,父亲就是扬场的老手。趁着风力,他端着木锨,双腿叉开,站在与风向成一定角度的上风头位置,借风用力,把混杂着碎麦秸和麦壳的麦子成一条弧线抛出去。碎麦秸和麦壳被风吹到一边,母亲站在那边及时用扫帚将麦秸和麦壳打落,剩下的便是几米长的一堆金灿灿的麦粒。扬完场,父亲早已汗流浃背。
那时候,麦收是农村人家的头等大事,从准备麦收到颗粒归仓,差不多得一个月辛苦劳动,一个麦收季才结束。现在的麦收,快捷而简单,收割机一进入,少则个把小时,多则半天,麦粒便哗啦啦地从机器里倾倒出来,装入麻袋,麦收季就结束了。相比于现在,那年麦收季里收割、打麦、晒麦过程中的艰辛与不易,时隔这么多年我依然历历在目。虽然在外工作多年,现在每逢麦收季,我总还要回家帮父母收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