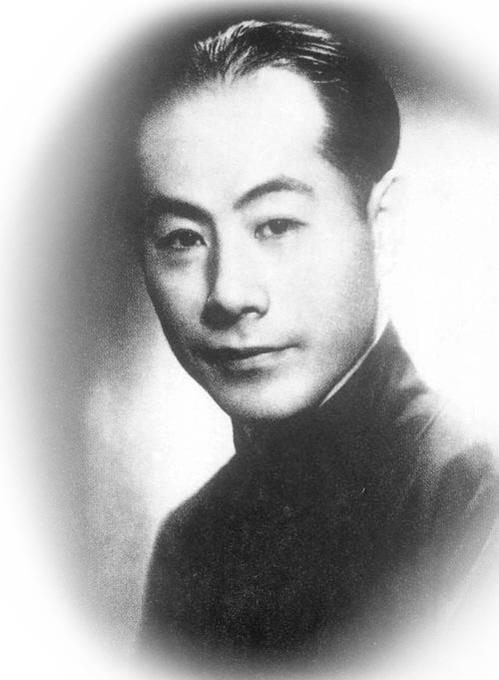(接上期)
王韵缃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敢作敢为。她和张伯驹结婚时,从娘家带来一个贴身侍女,这个侍女是立了卖身契的。王韵缃过了门以后,就当众撕毁了这个侍女的卖身契,并把这个侍女看成亲妹妹,后来,就叫自己的儿子喊这位侍女为小姨。
王韵缃在天津家里安排好长辈、孩子生活的同时,也惦念着丈夫的生活。张伯驹当时在北京、上海盐业银行的俸禄有限,王韵缃就常把盐业银行的股息转账给他,以保证他的开支。张伯驹逢年过节回天津,也都是由王韵缃安排一切。有时,王韵缃也带着孩子去北京看望张伯驹。
应该说,张伯驹和王韵缃婚后的一段生活还是很和谐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张伯驹有一首词《念奴娇》,注明“中秋寄内”。有人考证说,张伯驹后来写给潘素的词一般都写“寄慧素”。那么其时王韵缃长住天津,说是写给王韵缃的,也是有道理的。这首词写道:
无人庭院,坠夜霜,湿透闲阶堆叶。月是团圞今夜好,可奈个人离别。倚遍云阑,立残花径,触绪添凄咽。满身清露,更谁低问凉热。
记得去年今日,盈盈双袖,满地明如雪。只影那堪重对此,美景良辰虚设。玉漏无声,银灯熄焰,总是愁时节。谁家歌管,任他紫玉吹彻。
这首词确实饱含怀念妻子的离情别绪。王韵缃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知识妇女,张伯驹何以会写出这样高雅的情词呢?笔者认为,一者是他同王韵缃确有新婚夫妇的相爱温存之情,二者也是张伯驹借着这题材,展示了他学习唐宋诗词的体会和成绩,是有意锻炼自己填词的能力。
当然,清官难断家务事。后来,在一段漫长的家庭生活之后,王韵缃曾起诉张伯驹,她在诉状中说,自她1927年生下儿子后,丈夫遂对她冷淡,置之不理,他们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妇生活。
诉状中还讲了诸多财产纠纷,要求张伯驹给她生活补助等。张伯驹在答辩中承认,“实际上已有十五年以上没有同居”,并提出离婚。但王韵缃不同意离婚,说张伯驹对她没有感情,她可以分居。她宁愿分居,也不愿离婚,显然,她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弱者,一个被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礼教扼杀了独立个性的妇女,的确是令人同情的。
这个时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2年了。王韵缃在天津原来就是认识吉鸿昌将军的遗孀吉红霞的。其时吉红霞是天津市的妇联委员,她非常了解张伯驹家的情况,新的婚姻法已经颁布,张伯驹怎好继续维持和潘素与王韵缃两个妻子的共同生活呢?在吉红霞的劝说下,王韵缃终于同意离婚,张伯驹给了她一笔钱,她就到已在石家庄市工作的儿子张柳溪那里去了。
王韵缃的确很善良,她离婚了,但对离婚从来没有过怨言。1988年,她79岁时去世。
伉俪情深
王韵缃生了儿子后,张镇芳就对张伯驹说不允许他再娶妻,但是张伯驹还是在上海遇见了令他一见倾心、成为知音的潘素。
张伯驹和潘素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才子佳人,他们的结合的确具有浪漫和传奇色彩。
20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盐业银行董事会推举为常务董事和总稽核,他可以到各分行视察业务和考核账目,他去上海最多,夫人王韵缃也打算随丈夫去上海,但张镇芳夫妇不同意,怕孙子留在天津得不到妈妈的照顾,又不允许她带着孩子去上海。
张伯驹只好一人在上海做事,并往汉口、南京等地查账。例行公事、接受招待之余,就要把时间消遣在他的艺术嗜好上。在上海盐业银行视察考核期间,不免要与朋友到娱乐场所花销。伯驹不喜欢饮酒,他叫的局只是听音乐,这就遇上了善弹琵琶的潘妃。潘妃的天生丽质和娴雅风度立时为张伯驹所倾倒。
潘素原名潘白琴,原籍苏州。苏州的潘家,本是世代官宦的大家族。其祖上潘世恩中过前清状元,官至英武殿大学士加太傅衔,潘世恩之孙潘祖荫在光绪年间官至工部尚书,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苏州百花行就是潘氏大家族的住地。潘白琴的父亲潘智合迁居上海后,时运不济,又不务正业,家道开始衰落,幼小的白琴常看见母亲以泪洗面。母亲为她聘请老师,教她习音律、学绘画。白琴天资聪颖,很快便初通音律并能挥笔成画。她13岁时母亲不幸病逝,来了一个冷酷的继母,好好歹歹过了两三年,还是把她卖到了烟花场,以演艺为生。
潘白琴沦落风尘,于上海西藏路与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因她弹得一手好琵琶,也能挥笔成画,尤其是骨子里透出的一种孤傲高贵,与一般女子不同,一时间在偌大的上海滩赢来一片赞誉。
张伯驹是精通古琴的,但他第一次听潘白琴操琴,琴弦一响,还是十分惊讶,想不到这样一位弱女子弹得如此出色,那说不尽的清雅远俗、柔美流畅,让张伯驹余味在喉。张伯驹心里再也抹不去潘白琴的身影和琴声了。
张伯驹青年时期长期生活在北方,前面已有三房妻妾,都不太如意,如今在上海遇到这个才貌不凡的女子,眼前一亮,神魄飞荡,坠入爱河。
不久,张伯驹在上海的朋友孙履安知道了张伯驹的心思,就充当了张伯驹这次恋爱的牵线人,使张伯驹和潘白琴有了交往。据潘素后来回忆说,当时看张伯驹有些“土气”,但很有才华,会画花卉,文化也好。随着交往增多,日久生情,以至潘白琴一心相许,非伯驹不嫁。因此,可以说,张伯驹与潘素的共同爱好和艺术情趣,是他们结合的纽带和情感的基石。
张伯驹与潘素是怎样结婚的呢?当年张伯驹还有一个朋友,是孙履安的儿子孙曜东,也是京剧爱好者。近年来,他曾口述往事,经整理出版了《浮世万象》一书,其中说到张伯驹和潘素的结婚经过。这一段话被寓真先生照录在《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中,我在这里也引用一下吧。
孙曜东是这样说的: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天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坠入爱河。
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笳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嵌了进去,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王昭君,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时潘妃已经名花有主,与国民党内一个叫臧卓的人正谈婚论嫁。谁知半路杀出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心跟定伯驹,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有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为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不像在北京、天津到处都有他们张家的一亩三分地。他只好又来找我。
那天晚上已经十点了,他一脸无奈地对我说:“老弟,请你帮个忙。”把事情一说,我大吃一惊,问他:“人现在在哪儿?”他说:“还在一品香。”我说:“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把她接出来。”
我那时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上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儿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到一品香,买通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把他们送到静安别墅。
孙曜东还说,事后担心臧卓会采取报复行为,却因孙曜东与汪精卫、周佛海拉上关系,为他们做事,而臧卓也投向敌伪,当了伪军某部的参谋长,两人见面后心照不宣,此事也就过去了。
一个无依无靠、从艺谋生的“青楼”女子嫁给了张伯驹,对于潘素来说,好像是涅槃再生,她的人生之路从此变得丰富起来。而对于张伯驹,他的婚姻生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他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从此充满了活力。他找到了一个具有共同爱好的妻子,一个在人生道路上能够互相关爱、互相鼓励,能够风雨同舟的妻子。
1932年,张伯驹与潘素在苏州结婚。这一年的9月29日,张伯驹夫妇拜过印光法师,将“白琴”改为“慧素”。从此,张伯驹便称妻子为“潘素”。
潘素结婚后最大的收益和变化就是一步跨进了张伯驹的“文化艺术圈”。大凡文学艺术大家,其一生必定与许多名人大家产生交集,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增长见识。
张伯驹早年的交友即多为文化界名流,除金融业外,他所交之友如袁克文、溥侗、方地山自是声名远播,其他如张大千、溥心畲、余叔岩、傅增湘、沈裕君等也都是艺术界颇有成就和声望之人,这一切都使潘素在艺术和学识上受到濡染和熏陶。
中国历代才女,能操琴者多,能吟诗填词者也多,但能绘画者却寥寥无几,即便有,也多局限于花鸟仕女,绝少画山水者,潘素则爱画山水,这是一条不易成功的路。张伯驹则鼓励潘素专攻山水。于是,张伯驹先是请老画家朱德甫教潘素从基本技艺入手,画一些花卉小品,为日后从事大创作作铺垫。张伯驹还请古文功底极深的夏仁虎先生教潘素学习古典文学。
就在苏州城里,还有一位名画家汪孟舒,此人学元朝黄公望,擅山水,于是,也被张伯驹请来,专门教潘素画山水,为潘素提供了常人无法企及的习画条件和环境。潘素学画生涯可谓漫长而艰难,她在张伯驹的支持下,付出了无数的艰辛,终于成为中国现代画坛上一位知名的山水画家,尤其擅长于金碧青绿及雪景山水、水墨山水、浅绛山水,兼南北宋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人评价她的山水画不染纤巧习气,不见刻板匠气,清雅空灵、气度恢弘、韵味高妙。据说,周恩来总理曾欣赏潘素的青绿山水作品《漓江春晴》,称赞说“此画颇有新气象”。
在绘画方面,张伯驹夫妇还互相配合,互为增辉,潘素擅画,张伯驹擅书法,于是,张伯驹常为夫人的画题诗、题词。二人以智者之思在丹青、翰墨间合作携手,寄托情怀,也折射出高贵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未完待续)
作者 张恩岭
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