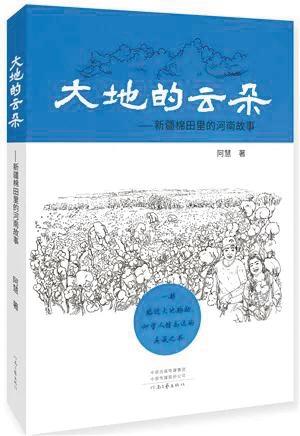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她喘口气说:“这几年,村里人都兴盖楼了,有的两层,有的盖三层,装修得明晃晃的。可是俺家里还是老房子,我结婚的时候,俺老公公给盖的三间平方,破鸡窝似的趴趴着。”
我说:“你也想盖楼房?”
她摇摇头说:“不想。别说没钱,有钱也不使到房子上,先供俩孩子上学哩。”
我问:“怎么想起来新疆了?”
她说:“村里有人要来拾棉花,有的来过几次了,劝我说,‘出去转转呗,拾花可挣钱哩。’我一听有钱挣,就立马报名跑来了。”
我说:“看来你是第一次来新疆拾棉花。”
桂花说:“是的。头三天累得我爬不上床,一接俺男人的电话就掉泪。儿子一接我的电话,也在那头哭。你不知道,儿子没离开过我的手。双方父母都去世了,两个孩子都是我一手拉扯大的。”
“我想家想得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梦里都是家。可是,早起一进棉花地,满地的花开得喜死人,每一朵棉花都是白花花的钱,抓一把是一把。这会儿,苦也不想,累也不想,儿女丈夫都不想,就想抓钱了。”桂花说。
我笑她:“真是个老财迷。”
她也不生气,说:“真的,老乡,俺真是来对了,在这挣钱多,我一天拾个六七十公斤花,老板一斤出八毛钱,俺一天就能抓个一百多,一个月就是四五千,两个多月的棉花季子,咋说也能挣个万把块。”
她欢喜地说:“你不知道老乡,前两天,俺男人打电话说,女儿想考研究生。我一听高兴地直拍大腿。你想啊老乡,研究生啊,搁从前那可是个大秀才。就对他说,让她考,可着劲儿考,闺女上到哪儿,咱就供到哪儿。缺啥也不能缺孩子上学的钱,小孩子上出来了,是小孩子享福,咱把累受过了,小孩子就少受。”
她看看我手里的笔,说:“俺就喜欢有学问的人,就巴望孩子比俺强。就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年轻人在大机器跟前一坐,手指在键盘上一呼啦,就把很多大事给办了。俺孩子要是能有那本事,俺两口子不吃不喝也高兴,梦里都会笑出声。”
大妹子自个儿笑出声,震得棉花朵子直颤悠。
这时,棉花地一阵骚动,许多人从花棵里站起,收拾棉花包。大妹子魏桂花说:“该称棉花了。”
果然见一辆大汽车停在棉田里,绿色的车头,后面挂一个大车厢。可能它早就候在那里了,只是我没有注意。我帮魏桂花把半包棉花,倒腾到一个大包里,俩人使劲地往下压,这包马上就成了喝饱水的老牛了。大妹子身子朝下一蹲,棉花包朝肩上一扛,弯着腰往汽车的方向走。棉花棵子刷拉拉一阵响,我站在原地流着汗喘息,只看到一个会移动的大花包,和花包下两只会移动的脚。
几十位拾花工,各自背着沉重的大花包,吃力地朝汽车挪动。有的姐妹,背了一包,又折回去背第二包。她拾得棉花比别人多,来回背包的趟数也就多。
太阳下,我的一双眼睛虚飘着,那带拖斗的大汽车,瞬间变成了一只白胖大蜂王,成群的小蜜蜂,扛着装满蜜的大口袋,嗡嗡地朝蜂王飞过来。
被踩平的空地上,放一个大台秤,还有一根由两个人扛的大杆称。地老板挨个儿称棉花,记录斤数。我挤进去,见一个女工大姐,正往本子上记数字,名字后面还有编号,编号的后面是斤数。后来才知道,大姐是队长,义务为拾花工记账,同地老板一天一对账。
大妹子魏桂花排在六十八号,她悄悄地对我说:“俺这编号真不赖,六是顺,八是发,俺六十八,顺又发。”
我笑她:“你还信这个。”
她说:“信。你没见今天的棉花数,俺多了二十斤,那是你帮俺拾的。”我一算,半天才拾了二十斤,一天才挣四十元。
大妹子说:“明天给老板说说,也给你几个棉花包。大老远跑来了,多少挣俩路费钱儿。”
“财迷女”真是掉进钱眼里了。我头摇得像拨浪鼓,我说:“我怕当全连第一名。”又说:“倒数。”
大伙儿又各自归垄,许是背棉花包耗费了不少力气,一时无人说话,棉田虚软下来。我本来打算去找那个记账的大姐,可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大汽车跟前,看准东边车轱辘下,有一片诱人的阴凉地儿,我坐在地上就不走了,背靠汽车大轮胎,身心有着松散的快乐。偷笑几声:“呵呵,歹毒的太阳,一时半会儿你是找不见我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