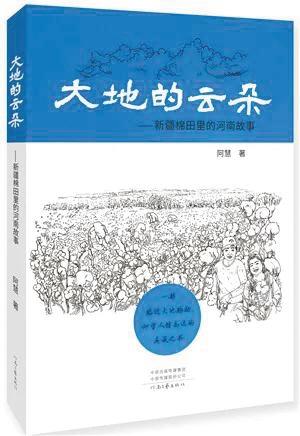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这人一放松就犯困,我倚着汽车的大轮胎,做了一个散发着橡胶气味的梦。我走进一个密不透风的大树林,每棵树腰都缠了一圈白丝带,我伸手去摸,却把手指黏住了,看上去白乎乎的,有股刺鼻的橡胶味。我正在梦中皱眉头,听到有人喊:“老板来送饭啦。”
我睁开眼,云朵被太阳晒散了,羽毛似的到处飞。地气蒸腾的热浪,在远处的棉棵上,形成几道透明的水波,哆哆嗦嗦地抖动,像人害了疟疾病。
一辆机动三轮车突突地开来了,一直开到大汽车旁边。一股黄白的尘烟,从土路一口气追来,带着阳光的激情,在我的身边打着旋儿。
我捂着鼻子站起来,把橡胶和土腥味暂时隔断。李大义正从车上卸下两只桶,一布袋馍馍,我赶忙跑过去帮忙。
李大义掐着腰朝远处喊:“吃饭啦!”声音粗粝,有股粗野和霸气。
姐妹们立马丢下活儿,小溪归海似地朝这里聚拢,边走边从自带的包里掏碗筷。说是碗,其实是铝盆,老板统一配发的,一人一个,就我没有。盆里有浮土,姐妹们用手一抹拉,筷子在咯吱窝里一夹一抽,就去打饭了。地上并排放着两只大塑料桶,白桶盛开水,蓝桶盛饭菜,我细看,两只都是带盖的涂料桶。
李老板亲自掌勺,说是勺子,其实是塑料水舀子。每人一舀子菜,一舀子正好一小盆儿。菜是冬瓜炖肉,冬瓜多,汤也多,肉不多,但毕竟有肉,大家伙儿蹲在棉棵里吃得很香,旷野有股食堂的味儿,馍菜里有股阳光的味儿。
这才发现三个男性拾棉工,他们躲开女工们,三个人吃得不声不响。
大妹子魏桂花端起饭碗正要吃,发现筷子不见了,她在编织袋改制的包里翻了翻,没有找见,可能是漏到棉花地里了。我正替她发愁,
她啪啪折了两根棉花杆,一双天然的筷子就有了,又从布袋里抓起两个馍,呼呼噜噜吃起来。我也从看不见颜色的布袋里,抓了一个馍。这馍比我的脸还大一圈,我有些矫情地对大妹子说:“这么大,我哪吃得完呀。”她顾不上搭理我。
我没有饭碗,就没有吃菜,即使有碗,这菜我也不能吃,我蹲在地上啃馍。没想到,馍馍竟然那么地香,只几口,一个大馍就下肚了。胃里还空出一大截。我拿眼角去扫馍布袋,那布袋瘪瘪的,看起来没有什么内容了,就伸长脖子瞅姐妹们,她们显然比我有经验,一只手抓了两个。大妹子魏桂花手里的大馍馍,眼看就要掉地上,却始终没有掉下来。袋里、地上都没有馍,我最终只吃了那一个。
李大义走到我跟前,歉意地说:“送饭时才知道老乡是回民,对不住啊!你吃这个吧。”大手里两个青皮大鸭蛋。剥开皮儿,一口咬到蛋黄了,流油,咸咸的香。大妹子魏桂花,这时才专心地看了我两眼,她拍拍地上的空棉包,让我坐上面,别蹲着,她自个坐在土地上。
午饭时间很短,没有人舍得浪费。他们站在水桶旁猛喝一气,再把自带的大塑料瓶子装满,急慌慌走了。留下一片压倒的棉花棵,几个屁股印。
李大义老板开着三轮准备走,他问我:“老乡走不走?等会儿就冷了。”
我看看太阳,还那么火辣,就说:“不回。”李大义就开着三轮突突突走了。
姐妹们拾花的速度,越来越显出差距,有的已经跑到了大前头,有的还在后面吊着,不像初到地时,排成大雁似的一字行,前行的队伍有点乱。
还想去找记账的大姐,发现她在最远的地边,我在棉花棵里走得磕磕绊绊,花枝子还不时扯上衣角不让走,我空着手出了一身汗。
大姐没戴大口罩,我仔细地端详了她两遍,确定这回不会错,就亲热地喊了声:“大姐。”没想到她比我更亲热,说:“累坏了吧妹子。”
我说还行吧,就下手帮大姐拾棉花。她说:“歇会吧,你不戴手套,手指头受不住。”我也发现了,这么热的天,他们都戴着线手套,有的露指头,有的指头也不露。
我说:“戴着手套抓不住棉花啊。”
大姐说:“第一年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了。”
我问大姐来几次了,她说:“除了八九年公家组织的那回,这五年一次都不少,年年来拾棉花。”
我说:“我想知道您的故事。”
她一笑说:“俺能有啥故事。”
大姐笑时,脸上有一对酒窝窝,虽然被褶皱网络着,但还是很迷人。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