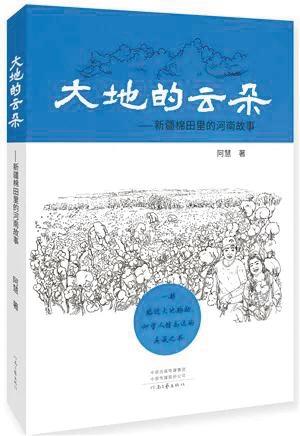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刘欢说,他弯着腰拾花,头勾得像豆芽菜,只一根烟功夫,脑袋就充血,两眼冒金星,白棉花变成金花花。那腰就酸疼得不是腰了,是一截子老柴火棍,一折就断似的。蹲在那儿拾花,比站着舒服些,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小腿肚子鼓胀得血脉乱蹦,双腿发麻,像过电似的。
这一天下来,拿捏得浑身疼。刘欢说:“不是活儿累,而是不畅快,说实在的,还不如去建筑工地出大力、干重活舒坦。”
我问他:“来新疆拾棉几次了?”
他说:“今年是第二年,去年俩月挣了一万三千元,算了算,还是比在家挣钱多。”
我说:“赚那么多钱回去,是娶老婆吗?”
刘欢的反应却像被蝎子蛰了似的,他白了脸色,连连摇头,说:“俺不想结婚。”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刘欢的媳妇定得早,那时他才12岁,就跟邻村的女娃定亲了,女娃比他小6岁,才上小学一年级。但刘欢喜欢这个“小媳妇”,上学替她背书包,放假帮她家干农活。结果他高中没考上,“小媳妇”却初中毕业考上了市卫校。刘欢到砖窑场拉砖,还往建筑工地送砖,积攒的钱给“小媳妇”送到城里,一直供养她中专毕业。
毕业后“小媳妇”又考上了一所大学,刘欢仍旧把打工的钱,一次次寄到省城,哪知人家大学一毕业,就跟人结婚了,刘欢这才傻了眼。那时,刘欢已接近30岁,村里同龄人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刘欢说:“她回来办喜事,我跑到家里去看她,在门外坐了一夜没敢进。那阵子我不吃不喝不睡觉,下着大雨朝外跑,坐在地上让雨淋,心里的大火日夜烧,快把我整个人烧成灰了。”
我说:“你那时就没想到她会离开你吗?”
他说:“咋没想到哩,村里人也劝过我,别再供她钱了,早晚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就是不信,我就是对她好,心想,人又不是狼,哪能那么心狠?”
刘欢的眼睛还是红了。时隔那么多年,那“小媳妇”仍是搁在他心头的一把刀,时不时割上一下。
没多久,有人给刘欢介绍了一个女人,女人离过婚,有一个5岁的男孩,男孩留给了男方,女人提着个小包,就在刘欢家住下了。家里有个洗衣做饭的,刘欢的日子开始热乎起来。他感激女人的好,就把在工地上掏苦力挣来的钱,一分不留地交给女人,谁知女人存起来,一分不留地给了自家的孩子。刘欢跟女人吵了一架,就把那女人吵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刘欢说:“有那么几年我不愿意相亲,一说要见面,心里就发憷,双腿跟面条一样软。”
有一个姑娘还是让刘欢动了心,比他小12岁,俩人一个属相。姑娘眉目清秀,文文静静,一口好听的四川话,让刘欢着了迷。姑娘来河南给表姐看孩子,想找个可靠的人过日子,她觉得刘欢这人还不错。
这回刘欢要明媒正娶了。他按当地的规矩给姑娘下了聘礼,“干礼”(现金)三万一,寓意是万里挑一。首饰是“三金”,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湿礼”不计,大鱼大肉随心意。
好日子定在2012年10月1日,结婚前一周,刘欢新郎官打扮,进城找姑娘领结婚证,哪知姑娘和表姐都没影了。房东说,她们3天前就退房走掉了。
听到这,我扔掉一大捧棉花,在原地来来回回地走,棉花枝条把我的衣裳扯挂得斯斯啦啦响,我心口像堵了一块大石头。若不是故事的主人亲口讲述,我无论如何不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假如被写成小说,读者会说这全是作者瞎编的。
刘欢的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他说,他明年还来新疆拾棉花,借人的聘礼钱还没有还完。
刘欢还是光棍一条。
我走向地头,面前是条被遗弃的水渠,没有了水,水渠就是死的,但芦苇让它活着。两条高高的渠岸,站满高高的芦苇,干涸的渠底被芦苇排满,是那种纯粹的黄。风来了,芦苇掀动一阵黄风,如水的波涛,水渠就有了黄河的模样。
太阳落山后,雾气大起来,棉田一片朦胧。寒冷蒙头盖脑地扑来,我在地头跺着脚,却跺出几声狗叫,叫声很远,也很短,好像被寒气冻紧了。
李大义老板也随着大卡车来了。姐妹们仍没有收工的意思,我渐渐没了耐心。疲劳沿脚底爬上了头皮,我昏头胀脑地钻进驾驶室。寒气小了些,但仍冷得彻骨,我抖着身子,后悔没在天黑前离开。
田野里突然一点一点的亮了,不知从谁开始的,一个接一个,半块棉地都亮了,灯柱时短时长。我有着不小的意外,贴近车玻璃去看,黑黢黢的田野,点点灯光晃动。
我忍不住跳下车,摸索着走过去,见拾棉工们的额头都顶着一盏小小的矿灯。矿灯照见的不是深井中的煤炭,而是黑暗中柔软的棉朵。光柱聚焦在面前的棉花,高挑的白色棉朵,跳动如梦如幻的芭蕾舞蹈。
拾花工们在棉棵里或蹲,或跪,瞪大眼睛,同灯光下的棉朵平视。没有人说话,连棉花枝叶都疲沓无声,只有他们疲惫的呼吸和若有若无的哈气。他们似乎把仅有的体力都聚凝在指尖,我听到,棉絮从花壳中抽出时细微的嘶嘶声。
每一朵棉花,都被拾花工手指抚摸,每一把棉花,都被拾花工手心温暖。
我有些明白了:为什么“手采棉”要比“机采棉”贵重?除保持了原始的棉质外,更重要的是,棉花和人最本真的情感。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