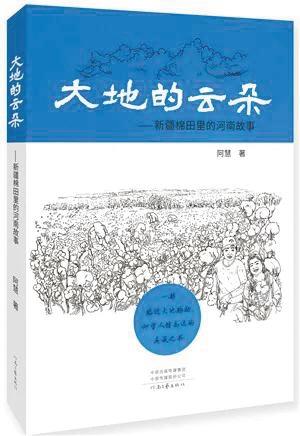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张书记微胖,面相淳厚。听完小张科长的介绍,他立刻让身边的宣传干事小张,安排我的住处,又通知后勤,给我另买一套新炊具。我内心滚烫,说给领导们添麻烦了。
张书记宽厚地说:“别客气,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他指着指身边的一位年轻干部,说:“刘明连长,也是你们的老乡,有事找他帮忙。”
刘明连长长得很板正,身杆子直溜溜的像天安门升旗手。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周口淮阳人,欢迎你老乡。”
又一个意外的惊喜,刚才还忐忑不安的我,现在就像站在自家的大客厅。
宣传干事小张和刘连长提着我的行李,送到二楼的小屋,小屋对着楼梯口,空间很小,七八平方米的样子。我看有张小木床,有一套桌椅,一个盆架,重要的是有暖气,还有一个电水壶,这已足使我幸福。
下楼来,领导们已在门外等候,上了车,一行人开往六场二十八连。两辆小车在地头停下,见一个人蹚着棉棵朝这走,一边走,一边跟我们打招呼。小张科长说,他就是这里的大工头张立,田里的拾花工都是周口人。
公路和棉田隔了一道水沟,沟里没有水,长满芦苇和杂草。我们一个个过了沟,蒺藜和芦苇花,不失时机地粘上衣裤,每人身上都毛烘烘。一个男领导,弯腰收拾裤腿上的毛毛刺,银灰西裤平平展展,连我都替他心疼,也从内心歉疚。
张立老板笑容可掬地说着话,满地的拾花工都朝这里看,我用一口地道的周口话喊:“老乡,俺来了。”
马上有人应:“哦,老乡来啦?中,中啊。”
送领导们过了沟,小张科长说:“要变天了,阿慧老师多保重。”
那表情,就像我一母同胞的亲妹妹。
两辆车远去,我走近拾棉花的老乡。
因为天阴,没太阳,这位大姐就没戴口罩,我就更直接地看到她的面容,除了拾花工脸上常见的晒斑外,大姐的脸色草纸般焦黄。她说话慢吞吞的,鼻音很重,一副厚道老实的模样。
她指着前头的人,说:“她们手脚快,把我撇到后头了,我拾花慢得很,手疼。”说着,褪掉手套让我看。
我一看,只冒冷汗。
大姐的十个手指头,除了两个小拇指以外,其它八个指甲盖全掉了,刚长出月牙似的新指甲,裸露的大半截肉红牙牙的渗人。我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二、冻得硬邦邦的柏油路
八朵花
“指甲姐”付二妮
付二妮,女,五十六岁。生育两个儿子,大儿子三十二岁,已成家立业;小儿子二十四岁,在南昌打工。丈夫五十七岁,在南京某工地做钢筋工,常年在外,收麦、种秋时才回家几天。
“指甲姐”说:“今年家里的几亩地包给人家了,老伴就不用回来了。我在家没事干,年龄大了,打工没人要。正好张立回咱周口招人拾棉花,俺就来了。咱老百姓闲不起呀,不是干这就是干那。大儿子不用管了,小儿子还没成家,还得花钱。”
她摇着头说:“现在,农村娶个媳妇可不得了,先盖两层楼,俺村里有人都盖三层了。还得给彩礼,干礼就得七八万,少说也要四五万。女方要多少是多少,你少给了,人家闺女不嫁了。为了俩钱,为了子孙,多抓几个是几个。”
“指甲姐”的手指都用创可贴裹住,拾棉花时有点笨拙,但她双手不停,稳抓稳拿,不急不躁。
她说:“人家都说,老婆纺花——慢慢上劲儿。我这是啊,老婆拾花——慢慢抓。”我被她逗得直笑,我笑,她也笑,大姐的笑声带有着浓重的鼻音,听起来像一架老风琴。
“指甲姐”他们四五十个拾花工,跟随工头张立,坐火车来到这九连的田地。地里的棉朵还没有开,张立老板就给他们找了个活儿,搓葵花头。按天工算,每人一天一百元。每个人腰里系个袋子,一手拿搓,一手拿葵花头,使劲地搓,葵花籽就掉进腰间的袋子里。
“指甲姐”干这活儿不得方法,指头里扎满了葵花的尖刺。这活儿干了一天半,他们又给老板家打葫芦。这葫芦就是当地的西葫芦,嫩时可以炒菜吃,长老后,打出里边的籽卖掉,据说,葫芦籽加工后可做美容品。
“指甲姐”他们进入葫芦地,用棍子把葫芦从秧子上打掉,用脚一个个踢到一边,两个人一排,都朝中间踢,手脚配合,就像棒球加足球,运动量很大。劳动的人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挥汗如雨。
长的圆的,灰的黄的西葫芦,在田间被踢成一行。老板按行子给工钱,一行子五十元,每行有七八百米。
这时,打葫芦机被大车拖到地里,葫芦机边走边打,葫芦籽当场装进袋子拉走,葫芦皮打碎后,直接倒进地里当肥料,滋养下一年的西葫芦。
“指甲姐”又打了一天半的西葫芦,夜里手指头一个个心脏似的乱跳。天亮一看,八个指头肿得像八个小灯泡,指甲盖被拱歪到了一边,浓水在指甲盖里面小鱼儿似的乱跑。轻轻一捏,血水就一股股地流出来。第二天又泉出水了,指头肿得要炸开。一姐妹用缝衣针一个个帮她扎开放水,而后用创可贴粘住,第二天就下地拾棉花了。
“指甲姐”说:“头茬花开得雪团子一样,像大铜钱在棉棵子上挂着,一抓一大把。我一抓手一疼,咬牙忍住,抓着抓着就不疼了。头一天就拾了一百六十斤,一百六十块到手了。四五天后,一揭胶布,指甲盖掉一个,一揭,又掉一个。有的连着一点儿肉,一拾花又挂掉了。不到两天,八个指甲盖全掉光了。”
我寒心着,又后怕着,如果大姐被缝衣针扎成脉管炎,或者破伤风,那大姐还是这大姐吗?
大姐却不这么想,她想的事情都如棉花一般的美和好。
她说:“夜里疼哭的时候,俺也想着回家,可是一想,人家张立,又是掏钱买火车票,又是免费让咱吃住,刚来几天,还没给人家拾几斤棉花就走了,这对不住人啊,钱短人长哩。”
我问:“家里人不知道你指甲盖的事吧?”
大姐摇摇头:“哪敢给他们说?家人知道了还要来人哩,还把我领走哩,不说,都过去了。”
我蹲在地上说:“姐,我心疼你。”
她说:“这有啥?咱河南女人能吃大苦哩。”
我坐在“指甲姐”的身旁记笔记,把大姐的话原汁原味地记下来,眼泪却一滴滴滚落,把刚写的字洇了一片。
地头有人喊我:“老乡,作家!作家,老乡!”我自顾自面对着本子哭笑,没有听到。
“指甲姐”说:“妹子,老板喊你哩。”
这才听见有人喊,站起来一看,张立老板正挥着手说:“老乡,来家歇歇喝口水吧。”
我大声说:“不用了,谢谢啦。”
“指甲姐”说:“这老板比老板娘强多了。你没见,老板娘整天噘着嘴,那嘴能栓头老叫驴。”
我帮“指甲姐”拾棉花,很快就追上了倒数第二名。那女子长得粗粗大大,声音也憨憨实实,见了我也不陌生,活像在一个村庄生活了半辈子。
她说:“你看他们这新疆,除了棉花,其他啥花也没有。”
我看看身边没有其他人,才认定她是在跟我说话,可能她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见个人就想说,这时正好见到我了。
我说:“我在地里也没有看见花,可能是秋天了,没花了。”
她说:“咱周口地里就有花,星星花,小菊花,狗尾巴花,啥花都有。”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女子想家了。
她说:“不知道俺来的时候,家里种的‘不死花’死了没有。”
我弄不清什么是“不死花”,她比划了半天说:“‘不死花’就是不死花,人家都死它不死。”
我觉得这女子有点憨。
果然她边掰扯手里的棉花,边粗拉拉地问我:“你是来新疆找俺的吗?”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说:“是找你的。”
她一瞪眼说:“咦,找俺弄啥?你又不是俺男人。”
我被她噎得直瞪眼,“指甲姐”朝我努努嘴,小声说:“她是个憨子。”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