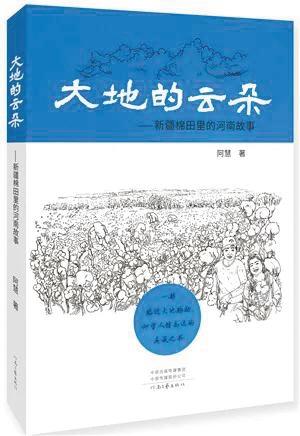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九朵花
“憨女子”柳枝儿
柳枝儿,女,33岁。她有一儿一女,女儿17岁,在读幼师;儿子8岁,念小学;丈夫在老家附近建筑队干活。
“柳枝儿”我在本子上记下这三个字,感觉一股清鲜的气息扑过来,我咬着笔帽说:“好名字。”将柳枝儿般鲜活的目光甩向她,却怎么也诗意不起来,面前的柳枝儿矮矮胖胖,分明是一截柳木墩子。
“指甲姐”说,憨女子小时候并不憨,7岁时掉到水井里淹着过,村人救起,放在牛背上控水,缓过气了,人就憨乎了。“指甲姐”说:“柳树枝儿插土就活,她这名字皮实。”
“憨女子”柳枝儿看起来很皮实,我正想问起她男人,她竟然竹筒子倒豆子地说:“俺男人给人盖房子搬砖哩,俺闺女、小子都上学,个个喝钱的货。”
我正要夸她好命,她却不让我插嘴,自顾自地说:“俺在河南老家没少给人打工。在足疗店给人端过洗脚水,在服装厂钉过纽扣,老板娘嫌俺钉得不好,不让俺干了。不让干拉倒,离了你这茅坑俺还不拉屎了?这不,俺就一蹦子跑到了新疆。”
“憨女子”柳枝儿突然捂住肚子,她拽下腰里的棉花包,一溜儿小跑去了芦苇丛,回来时脚步虚腾腾的。
她喘着粗气说:“俺一说茅房就想拉稀,这一个多月肚子没有好的时候。天天给老板要药吃,药也堵不住,说是水土不服。俺在家三天拉一回,在这一天拉三回。身上的力气没有少,还是可有劲,就是耽误拾棉花。你看,俺跑出去一趟,人家超过一大截,她们都快拾到地头了,俺还在这半腰里。”
我说:“少拾点棉花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这肚子,得赶紧治治。”
没想到她一瞪眼说:“那可不中,俺得抓钱给儿子看病。”
我一惊,问啥病。她说:“脑子里长个瘤子,医生说先吃药输水,过一段看看再开刀。”
这可是个大负担、大苦难。我紧皱眉头说:“那可是要花一大笔钱,你们两口子该怎么挣啊。”
她又一瞪眼说:“能咋挣哩?俺一毛一毛地抓,一块一块地挣,只要手脚不歇,俺孩儿就有活命。”
我劝她说,儿子不会有事的,药物治疗一阵子,说不定就不用做手术了,再说,国家还有大病保险呢,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次她没有瞪眼,低头盯着棉朵说:“都怪俺命硬,家里养啥啥死。养羊羊病,养鸡鸡瘟,就连俺栽在院子里的花,没等打骨朵就死了。连俺老公公也开地去了。”
我问:“开地?在新疆吗?开几亩?”
她又把眼一瞪说:“死了,在地底下干活哩!”
我吓得一哆嗦。
正巧“指甲姐”背着棉花包经过,她说:“别拾啦,吃饭了。”
我站起身一看,两个年轻人抬着饭朝这边走,身后是一片矮矮的村庄。我上前帮“指甲姐”抬棉包,二十几个拾棉工,蹚着棉花棵子都朝地头走。
这是一片空地,地上戳着小半截干枯的葵花杆。在我还没到来的时候,这里曾开满了金灿灿的大葵花,那花盘比胖媳妇的脸盘还大,一圈的大花瓣,就像是包裹着黄锦缎。这一大片的大葵花,就这样朝着天上的大太阳恣意地盛开。
我正在大葵花中迷醉,大伙儿呼啦啦围到了饭菜旁。一大盆煎豆腐,颜色黄黄白白很动人,豆腐比汤多,浓郁的香味很诱人。有人从包里掏出大碗开始自己盛饭,一勺又一勺,冒尖一大碗,又去竹筐里拿馍馍,一看是炸油饼,黄哒哒、香喷喷,刚出油锅的模样,下手就更猛。手指烫得一缩,却又立马伸出,拎一个饼在半空,一口咬个小月牙,两口一个大月牙,三口下去就剩半个了。
其他人也挤着盛饭,场面很活跃,把送饭的小夫妻挤到了一边,小媳妇的肚子脸盆一般大,小丈夫把她拉到身后。两张仍显稚气的脸木楞愣的,看来他俩是第一次来送饭。
我正呆呆地看,“指甲姐”端着饭菜用胳膊肘碰碰我,说:“你的碗哩?还不快去盛饭。”
我摸摸布包,掏出一只小碗,“指甲姐”挤过去帮我盛了,递给我说:“瞧你这小碗儿,像个鸡蛋壳,一看就不是掏劲的人。”
我端着豆腐闻了闻,“指甲姐”翻了我一眼说:“还不吃?闻闻就饱啦?”
我说担心里边有大油。她“扑哧”一笑,说:“俺来40多天了,连个荤腥都没见。别说大鱼大肉了,就今儿这豆腐,还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
她指了指空地说:“这片地是老板种的葵花,收了不少葵花籽,吃的都是新榨的葵花籽油,想吃别的也没有。”
这时,“憨女子”柳枝儿扛着大棉包拖拖沓沓回来了,她把包往地上一墩,浮土腾起来,吃饭的人赶忙捂住碗口。“憨女子”端着大碗去盛饭,她弯腰看看盆,又看看筐,突然把碗一扔,一屁股坐在地上嚎:“俺的饭叫谁吃了?咋没饭啦!”
我不安地看看自己的碗,那年轻的男主人白了一张脸,他不安地看着地上的“憨女子”。“憨女子”两脚轮换着乱踢腾:“俺就拉一泡屎的空儿,饭就没了。这下好了,肚里没食想拉也拉不出来了。”她拉来拉去的,大家伙儿谁也吃不下了。我越想越觉得抢了人家拾棉工的饭,就连忙端着碗送到“憨女子”面前。
小男主人拦住我说:“你吃吧,家里有,我带她回去吃。”
小夫妻抬着空盆走了,“憨女子”柳枝儿端着空碗跟在后头,裤子上的泥土一走一掉。
一群人又往地里走,有人从葵花茬子里急火火走过来。她50来岁,穿一条黑色胖腿裤,花格子棉马夹,粉色围巾裹住头,围巾的两个角,在脑后一走一颠,她边走边喊,一口正宗的周口话:“你说这像话吗?饭不等人盛就抢了,有人撑着,有人饿着,这像个啥?俺儿气得脸蜡白,俺儿媳妇气得在家哭,看你们都干的啥事?”
她在我不远处站下,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右脚向前一步,脖子一探一探地说:“今儿来人了,你们就给我办难看,让人家作家都写上吧,看看谁难看!”
地里没人吭声,大家各干各的活儿,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
我听见了,明白她是专门说给我听的,就拍拍旁边的布包让她坐。她低头走过来,不坐,蹲在那生气。她的花白头发从头巾里露出来,眼角的皱纹像打开的折扇扇骨,眼睫毛倒是又密又长,随着粗重的呼吸,忽忽闪闪。
她转过脸对我说:“你说说老乡,这是不是给我办难看哩。几天前,他们说,老板娘咱做顿豆腐吃呗,想吃豆腐了。我就跑了几个村,在咱永丰老乡开的豆腐店里买豆腐。听说你来了,我又用新榨的葵花油,炸了一篮子油饼子,一人一个,算上你,还该余剩四五个。结果,你看看……”她两手一拍,“啪”一声,又摊开。
我说:“都是自家人,肉烂待锅里,吃多吃少这都不是个事儿,大家干活都起劲儿。”
老板娘说:“说起拾棉花,咱周口人最死守,从天明到天黑,待在地里不停歇。一块地,一两天拾了个精光,这周边找咱拾花的老板排长队,还有几家没有排上号。就是有个小缺点,不拘小节,缺少规矩,这是在咱自己家,要是在其他地方,怕人家背后笑话咱。”
我不由得对老板娘心生敬意,她提到“小节”,讲到“规矩”,是对家乡,对姐妹们更深层的爱。
我说:“嫂子,你讲话这么有水平,起码是个高中生吧。”
她揪住围巾的一角掩着嘴,笑的模样很羞涩。她说:“说起来怕老乡你见笑,俺满打满算才上了一年半的学。家里姊妹多,父母不让女孩儿上学,长大找个家嫁了就算了,让俺在家照护俺弟弟。可是俺就是想念书,天天背着弟弟去学校,站窗户后面听念书,听着听着就会了,用小棍子在地上写字。一个女老师看见了,问了俺这,又问俺那,没有俺不会的,她就准许俺背着弟弟来上学。俺一年级上了一半,就直接跳到三年级,后来俺娘不让俺上了,嫌俺没照看好俺弟弟。可是俺爱看书、爱读报,地上有个带字的纸片,俺都拾起来念一念。俺还学会了查字典。不瞒你说,自从1993年来到新疆,往家寄的信都是俺写的。教书的侄娃子说,俺姑写的信一个错别字也没有,用词造句很得当。”
我被她感动,说:“没想到嫂子你那么爱读书,现在没多少人喜欢读书了,他们都爱数钱了。回头给我个地址,寄书给你。”她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那可比啥都主贵。今儿听总场领导说,要派个作家来俺家,俺又高兴又担心,担心俺水平低,让你看不起。”
我也拉上了她的手,老板娘的手骨节很大,手掌心涩拉拉的像砂纸。
天仍阴沉着脸,我和老板娘越谈越热乎,越坐越寒冷,她抖抖肩膀说:“刚才一生气跑出来,没有穿棉袄,这会儿怪冷的。咱回家边做饭边说吧。”
我催促她快回去穿衣、做饭,自己站起来去追姐妹们的背影。这时,大路边的杨树一阵唰唰地响,黄树叶纷纷飘落,冷风扫过来,我浑身一激灵。
刚来到地边,就听见一个女子在说话,声音清灵而温柔。我轻轻地走过去,见她一手抓棉花,一手打电话,白口罩在右耳边晃荡。她说:“好,乖儿子,妈挣钱了给你买。你妹妹呢?唉!妞妞,妈也想你啊,好,买棉袄,吃饱饭,妈妈记住了,好好听爸爸的话……”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