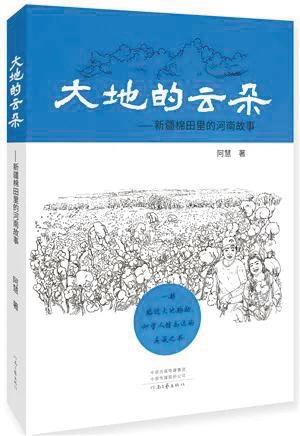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她说:“末了,我还是遇上一个麻缠的主儿。扒开产妇腿一看,不是黑头顶,是一只小红手,还抓呀抓的。我的妈呀,吓得我冷汗哗地下来了,布衫子都溻湿了。这娃是要抓走她娘的命哦!我就轻轻牵住那小手,送回她娘肚里。正要伸手转胎位,谁知又掉下一只脚来,吓得我一屁股把热水盆子坐翻了。眼看产妇没一丝气力了,我说,你们骑上马去医院吧。她家人说,‘那么远,会颠出人命的,嫂子你还是想想办法吧。’我一咬牙,一狠心,把胎儿转磨个头朝下,一按肚皮,孩子出来了。浑身乌紫,打了十几下脚心,这才哭出声来。”
我听得身上发冷,脸上发烫,很想喝口水,可是月清嫂不留给我插嘴的机会,她好像要把这二十年的经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这倾诉的闸门一经打开,就像她亲自扒开水口似的,一时半会儿很难堵住。
我不想堵住,我只想倾听,我很想倾听。
月清嫂说:“打那起我不再接生了,后来条件好了,生娃娃都去大医院了。”
她沉思一会儿说:“作家妹妹,你说怪不怪?我接生的八个娃娃,现在都是大学生,我这双手应该是当老师捏笔杆的手,你看,我摸过的娃娃个个学问大,有文化,我说的对吧!”
我终于可以回答了,我说:“对!很对!赵老师。”
她用右胳膊掩嘴笑,伸出左手来打我,我一边躲一边想:我十八岁当小学老师,几十年没爱上这职业。月清嫂却想当老师,想了一辈子。
我向月清嫂投去敬重的眼神,她望着灰突突的天说:“这天恐怕要下雪了,千万别下大了,人进不了地,可就麻烦了。白花花的好棉花收不回来,那可是真要人的命啊。”
她说:“有一年下大雪,大片的棉花都没拾回来。还有一年……”
月清嫂随上那场飞扬的大雪,给我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十四朵花
“蜻蜓女”杨大秘
杨大秘,女,出事那年三十五岁,河南某县农村人。生有两个男孩,大概十来岁,丈夫在家务农。
月清嫂说:“这件事发生在十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正是拾棉花季节。这女子我也只过一面,不清楚她是咱河南哪个县的。她来过我家,找她认识的一个拾棉工,当时就站在这棵柳树下,没说几句话就走了。单眼皮,薄嘴唇,挺白净的一个女人,出事后才知道她叫杨大秘。
“那时,俺家有百十亩棉花地,俺男人回老家领回十几个拾棉工,跟现在一样,给谁拾花,谁管吃住。那天一大早,王连长来我家问,‘你们家的花工少不少?’我一听,身上直发毛,问,‘咋回事?’俺男人也出来了,重新查了一遍人,说,‘不少,还是十二个人。十个女工,两个男工。’连长骑着摩托车走了。
“没多大会儿,村人说,西南地边杀死个人。我撂下手里的东西跑去看,公安已经用布条围起来了,一个女的躺在那儿,没头了。
“清早,雾还大着,天格外冷。连长骑着摩托车在地头转,看看哪块地的棉花开齐了,好派花工去捡拾。这时他发现,棉地边有个黑东西躺在那儿,就想,这是谁家毛驴卧在这儿,一夜还不给冻死?他以为头天晚上,毛驴找草吃,卧路边没回家。那时,家家都使毛驴车,喂的都有毛驴,我家也喂了两头。我也学会了使牲口,赶驴车。
“连长走近一看,是个人,没有头。赶紧回连队汇报,警察围住,侦查现场,挨个问工头,谁带的人少了。很快查到前头那家,他带来的人里,少了一个叫杨大秘的女工。三十多岁,有两个男孩。结果,这户工头家的十几个花工全带到连部去了。
“办公楼上,大灯泡在头顶上照着,公安人员对他们一一盘问。最后,只剩下了六个人,其中一个浑身发抖,头冒大汗。一审他就交代了,说人是他杀的。”
我惊住了,端起茶杯一口气把水喝完了,月清嫂也喝了一大碗。原本,一片金黄的柳叶在她碗里小船似地飘,她也一股脑地喝进去了,拿柳叶当茶叶在嘴里嚼。
我伸长脖子问:“为什么杀她?”
月清嫂把柳叶咽下去,拍拍我说:“你听我说。”
“这里边还牵涉另一个女人,她是杨大秘的大嫂,妯娌俩一起来新疆拾棉花。没几天,杨大秘就发现,嫂子晚上总是出大门,到野地去解手,一解就很久,有时她迷迷糊糊睡着了,旁边嫂子的床铺还空着。
“这天,刚吃过晚饭,杨大秘就瞅见一个男人站在暗影里,冲她嫂子咳嗽了两声就闪出大门了。不大会儿,嫂子裹着棉袄出去了。杨大秘跟随他们出了门,大雾里,这一男一女走得飞快,一晃就消失在棉田里。杨大秘蹲下身子,听见棉棵子一阵哗哗响,嫂子的声音像哭又像笑。杨大秘也是过来人,她明白了棉花棵里发生了什么事。你想啊……”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