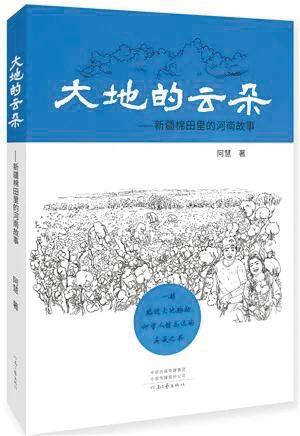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她又朝我走两步说:“老乡你猜咋的,绒线走后半个月,我下头也突然出血了,开始以为是例假,没想到,沥沥拉拉十来天,血的颜色鲜滴滴的红,身上力气像抽丝,一点点被抽走,手脚软得像棉花,这才找老板要药,去诊所看病,一看,也是环掉了。只是我比绒线幸运,那环顺当排出来了,只是子宫有炎症。我天天吃着药,花了二百多块了。这几天出血少些了,就是小肚子又凉又沉,向下坠着痛。刚才车上一颠簸,感觉子宫就要出来了。”
我头皮直发麻,说:“那还不赶紧回河南,看你这脸色,像树叶一样青黄,到底要钱还是要命啊!”
她说:“起初我也打算走,可是想想咱来一趟新疆不容易,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啊。来时天还热着哩,绿皮车没空调,人又多,整个车厢满满的,都是拾棉工。过道里躺的都是人,横七竖八,没有下脚的地儿。上厕所像探地雷,一点一点往前探,一不小心踩上人的手和脚,乱骂乱叫唤。没让尿憋死,也被人吓死。那车上啥气味都有,让人出不来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天天趴在窗口边,看天明了,又又黑了,我的亲娘哎,这新疆咋会这么远,走到天边了吗?”
说起坐火车来新疆,我当初也有这计划,打算和拾棉工一起搭伙来,路上也热闹。但是时间不凑巧,比他们来得晚。为了赶时间,我就改乘飞机追来了。
陈银行说:“你说咱来一趟那么难,有个小病小灾的,能忍就忍了,人能留就留了。那么远来干活,哪能不干完就走的。最起码不能一个人走,大家伙儿一个车皮拉来的,还要一个车皮拉回去。再坚持一二十天吧,有始有终,那才叫中(行)。”
陈银行手里的节奏更快了,说:“我这一天不急不慢地拾六七十公斤花,抓一百多块钱,好着哩!摸一块,是一块,拾一棵,是一棵,拾了还想拾,摸了还想摸,不摸白不摸。”
这哪里像个病人,人的精神力量有时真的很强大,大得让人不可思议。
陈银行指着前头说:“你看这满地的花都开着,多喜欢人儿啊!今天拾了,明天还想拾,手脚停不下来了。说实话姐,我这心里矛盾着哩,肚子疼时,想着早一天拾完花,早一天能回家。一到地里,又恐怕把棉花拾完了,钱挣少了。拾着这块地,望着那块地,眼贪、心贪、手也贪,就是贪抓几个钱!”
我说:“你家有车有房,儿女也都成了家,按说你日子松快了,该去打个牌,跳个舞,为啥还那么拼命挣钱呢?”
陈银行一扬眉毛说:“人长脚就得不停地往前走,人长手就得不住地往上爬。刚有了几顿饱饭吃,就停下来不走了,那生活还有啥意思。我和俺老公说好了,今年把小货车贷款还完了,明年再贷款买个小轿车,我开着轿车来新疆拾棉花,把车头贴满玫瑰花。”
我被她离奇的想法迷醉了,直着眼对她说:“我想,那该是一辆新娘花车,车里坐着你这枚玫瑰旧娘。”
“玫瑰女”陈银行捂着肚子,鼓着腮帮子笑,说:“俺不是旧娘,是老娘,俺都当姥娘了,哈哈哈。”
在这片广漠辽阔的土地,我喜欢看见老乡们的笑,就像喜欢看天上的白云朵,地上的白棉花一样,这纯美而柔韧的白,不经意的还原了我灵魂深处的底色。
天上没有太阳,空气有些干冷,毛渠边几棵高挑的白杨树,把树尖上仅有的几片黄叶交给了风,树枝一阵紧密地摇晃,唰唰唰,我赶忙把头巾系紧,怕风像摘树叶似的,摘掉我凌乱的发丝。
就这样,我弄丢了我的水笔。
蹲下去拨动棉花棵,在原地仔细地找,只见草杆,棉杆,就是不见我的笔杆。这意味着,接下来的采访,我将无法用文字记录。虽然携带有录音笔,还有笔记本电脑,但我仍然习惯和信任用黑色水笔在纸上记录,与文字面对面,就像和拾棉工老乡面对面一样,让我感到温暖和踏实。但此时我丢失了我的笔,我的手和心,都似那股游动的风,寂寥而空荡。来新疆时,我特意准备了一盒黑色水笔,一个精致的仿牛皮笔记本,半个多月的采访记录,笔尖在纸上不知疲倦地游走,绵延出一行行蜗牛般持续不断的足迹,每一行凌乱无序的小黑字,无不散发着最原始的本真草木气息,我在这真纯的气息中,一天天回归真纯。
“我这有只笔,你看能用吗?”我听见一个沧桑的声音,随见一只沧桑的手,一只小巧的圆珠笔伸向我。我一下子认出了,他是“上门男”白路根的同伴,也是仅有的两个男性拾棉工之一。
我接过圆珠笔,有些意外,有些感动。我说:“谢谢你大哥,这笔……”他说:“哦,我用它记下每天拾到棉花的斤两,心里好要个数。这笔不太好,你先用着吧。”
看来这大哥,早把我满地寻笔的样子看到了,真是一个有心人。
十七朵花
“有心男”邓金国
邓金国,男,五十六岁。生育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三十四岁,老二三十二岁,女儿二十八岁,都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老婆二十多年前跟人跑了,至今遥无音讯。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