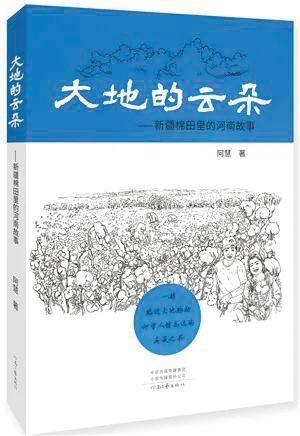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天蒙蒙亮,人和车来到了刘庄店地界。二伯家的小儿子,我未谋面的建立哥哥,闪着车灯在路口等。他除夕夜几乎没有睡觉,电话始终同我保持联系。我和建立哥下车拥抱在一起,同时感觉一样的心跳,一样的血脉奔流,兄弟俩同时泪流满面。”
“我刚到村口,红红的鞭炮响了许久,村路像铺了一层红地毯。烟雾中,我双腿绵软地朝家走,几位老人上前抱住了我,一声声‘明明,明明’,那声音、腔调,跟父亲用河南话唤我时一模一样。”
“在二伯家吃了一大碗饺子,这大年初一家乡的第一顿饭,是父亲多少年来的渴望和梦想。我每吃一个饺子,都在心里对父亲说,‘爸,再吃一个。’捧着碗不敢抬头,怕眼泪掉下来。”
“大娘铺好新被褥,说让我赶紧补补觉,毕竟开了一天一夜的车。我说,我要先去看望爷爷奶奶。掀开后备箱,取出我老婆准备好的烧纸和水果,还有一瓶伊犁大曲。一行人走出村子,走进田地,远远地看见,一大片绿莹莹的麦苗中间,突起几个土坟包。我的双腿突然变得很沉重,像绑了两个大沙袋。我一步步拖着自己走,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这几座圆尖的坟包,睡着我的祖爷爷、太爷爷,还有我爷爷,我知道我的根就在这里,我的血管流着他们的血,我在遥远的新疆延续着他们的生命。我跪在爷爷的坟边,按照老家的习俗,摆水果,点烟,烧纸,放鞭炮。我倒上两杯酒,想像着从未谋面的爷爷奶奶的容貌,我说,‘爷爷奶奶,明明回来看你们了,我回来得太晚了,您老人家别怪罪,孙子给你们磕头了。’旁边的婶子大娘小声地哭泣,我端起酒杯说,‘爷爷奶奶,我替爸妈敬你们一杯,他们俩没能在你们的身边尽孝,请爷爷奶奶原谅。这第二杯酒,是我和媳妇孝敬您们的,爷爷奶奶请接受。明年,我带上媳妇、儿女一起回来,一起过春节,一起给你们拜年。’这时,建立哥领着一群小孩子,燃放起了烟花。二伯说,‘咱家明明回来了,是老房家的大喜事,列祖列宗,咱都庆贺庆贺吧。’”
房明的眼睛红红的,我能体会到他的感受,就像深深地懂得那片土地。我随着房明的话,仿佛跟随他回了一趟河南老家,那片温暖厚重的土地,孕育出一代代朴实厚道的人,犹如那永不停息的沙颍河水,安静而平和。
刘明说:“我的父亲和房哥的父亲一样,都是当兵来新疆,只是我父亲要年轻几岁。这几年高铁和航运都发达了,我们父子轮流回淮阳,奶奶早几年去世了,爷爷跟着我大伯住在龙湖边,龙湖可不是芳草湖,那湖水满满当当,我蹲在老房子的后边,那水就漾到房根脚,清凌凌的湖水,能看见小鲢鱼。”
房明,这个26岁当连长的精壮汉子,谈起家乡来,声音和表情都是那么的灵动,就像一条小鲢鱼,在家乡龙湖里欢快地吐着水泡,一串接一串,在散满阳光的水面上轻微爆裂。
房明和刘明,两个年轻的兵团干部,他们的父亲都是献身边疆的老军人,老少两代军人,一样的志向,一样的乡愁。
刘明说:“兵团老一辈人这样说,‘我为边疆献青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
无意中,我注意到了房明的门牙,虽然被香烟熏得灰黑,但总感觉有些异样。房明发现我在看他,赶忙闭上了嘴巴,把刘明笑得直拍桌子。
我说:“是喝大酒磕掉的吧?”
刘明替他说:“五年前,房哥用药拌棉种,不知不觉把两颗门牙腐蚀掉了。”他指了指房明的嘴巴说:“那是后来补上的假牙。”
张干事说:“他老婆一年多不愿跟他亲嘴儿,担心把他的假牙亲掉了,咽进肚里不好找。”
几个人又是一阵笑,房明在桌下踢了张干事一脚。
刘明说:“房哥的头发也被腐蚀掉了,光秃秃的,花了不少的钱,去年才长出来新的。”
我没笑,心底泛起无言的沉痛,看着他们年轻的笑脸,这笑容里蕴藏多少苦涩,多少担当。
饭菜剩了不少,我说:“打包带走,我这几天有饭吃了。”
张干事看了我一眼,说:“凉菜怎么吃?”
我说:“没事,热热就行。”他就把剩菜提上了车。
返回的途中几乎不见车,那么宽的路,好像只为我们这一辆车铺就的。张干事驾车任性地跑,我总感觉路途比来时远,估计该到了,但路前头还是路。
我问:“咱们来时就这么远吗?”
刘明说:“是的,从六场到芳草湖80里地。”
来回夜行160里,只为请我这个远道而来的老乡吃顿饭。我想,有比路程更深远的东西,那就是深远的土地根脉。
房明他们把我送到楼下,我交代张干事,回去路上开车慢一点。见他们上了车,我突然想起打包的菜,估计张干事感觉送我剩菜不合适,我也没好意思张口要,感觉那样更不合适。三个人从车窗里伸出手,我站在台阶上也朝他们挥手,只见两束黄白的光柱刺破夜幕,越闪越远。
进了小屋,暖气不热不凉,脱掉羽绒袄,坐在床边,我还惦记那包菜,后悔刚才没有再鼓鼓气、张张嘴,把剩菜要回来,明天在食堂热热吃,还能解解馋。
自个儿偷笑一会儿,也暗自数落自个儿一通:“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俗气、贫气、贪吃了呢?真让人脸红。”
我赶忙照镜子,镜子里一张青黄青黄的脸,一点儿也不红。
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把记录本放腿上,刚写了几行字,哪知身子不听话,软软地倒下了,却倒在一个棉花堆上。我的四肢尽情舒展,感觉身体一丝丝融化进棉团里,能听见骨骼细碎的咔咔声。我竭尽全力地发出声音,我毫无分量地躺在那儿,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棉田,密集的棉棵不知哪儿去了,白棉花铺满一整块田地,水纹般颤抖的雾气中,一群姐妹背着饱满的大棉包朝这边走,白雾绞成缕缕丝线,牵绊她们的脚步,她们的喘气声越来越重,一声响过一声。走近了,我努力分辨一张张汗淋淋的脸,“酒窝姐”“被拐女”“耳环女”“指甲姐”“憨女子”。她们没看见躺在棉花堆上的我,也没听见我无助的呻吟,她们什么也不看,纷纷解开大棉包,朝我一股脑地倒棉花。那棉花真多啊,一包包倒不完,我被棉花埋住了,感到了胸口的憋闷和沉重。我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
“啪”地一下,我在梦里打了个激灵,醒了。我睁开眼,头顶一枚耀眼的小白灯。我从棉田回到了小屋,我穿着衣服仰面躺在床上,右手还老实地放在胸部。记录本滑掉在地上,我翻身下床,弯腰捡本子,全身骨骼细微地响。我直起腰,大口呼吸,这才感到一阵内急。
自从在四场有过深夜摸旱厕的骇人经历后,我不得不在饮食上苛求自己,晚饭坚持少吃,最好做到不吃。虽然是在拾棉工集聚地,我几乎是饭菜没得吃,但我还是很小心,尽力做到不起夜,一觉睡到大天亮。但今晚是次例外,那么好的老乡,那么好的饭菜,虽然我筷子“搛”得不是那么勤,进肚的美食不是那么多,可是,我那贫瘠多日的肠胃,一时间还耐不了富贵,容不得荤腥。
我披上厚衣冲下楼,什么都顾不上想。可是有时候不想也不行,因为楼下大门紧闭着,我上前一推,没推动,低头一看,上了一把大链锁。我心里一紧,小腹一收,心跳加速,身上起了一层冷汗。怎么办呢?我发现旁边一小门,一晃,开了!还算幸运,我正张嘴笑,一股寒风冲到嗓子眼,噎得我差点儿出不来气儿。冷风还想抱住我的腿,我利索地把它撇开了,它失望地贴住台阶打着旋儿。
大门前有盏灯,挂在高高的水泥杆上,头上戴个大碗似的灯罩。有限的光以大门到花台为半圆,画着昏黄的圈,厕所在圈外。我冲出光圈外,走进小树林,沿着石子路,迎面站立墙头似的枯芦苇。我高举手机,让手电筒的光劈开芦苇丛,其实这茂密的苇丛,早已被如厕人的脚从中劈开了,被踩倒的苇子和草走上去软软的。寒风送来了一股异味,期盼中的厕所到了。厕所门前没有灯,或许是有灯,正好坏掉了。我站在黑乎乎的厕所门口,不敢朝里走,我能想象得到,这黑乎乎的旱厕里面,将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心理上生出的障碍,一时超出生理上的需要。我扶着墙干呕了一阵,脑袋呕得缺氧,眼珠子直往外鼓。
闭口气冲过去,马不停蹄地冲出来,踩过哗哗响的干芦苇,踩过高低不平的石子路,踩进路灯的黄圈里。我深深吸吮冰凉的空气,远望夜幕下模糊的村庄,近望二楼我那间小屋暖暖的灯光,听一两声狗叫,感觉这清冷的夜晚是如此的可爱。
睡梦中有人敲门,我以为还是在梦中,就闭着眼,躺床上不动。门又响了,我趿拉着鞋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中年妇女。门外很亮,我眯着眼看她,像看一个剪影。她用生硬的普通话说:“该吃早饭了,等你吃饭呢。”
我赶紧把女师傅朝屋里让,她摆摆手下楼了。
饭堂就在楼后边,上次张干事交代过我,只是我一次都没去。我捧着小碗往后走,见两个人吃完饭走出来,我见他们很面生,就点点头走过去。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回头说:“是作家老师吧,快进去吃饭吧,马上就要关火了。”
我说:“好的,谢谢领导。”
女师傅正在擦桌子,见我进来,赶紧过来打招呼。她领我到灶台前,从柜子里取出一口挂着吊牌的小炒锅,炒锅里一个新锅铲、一个新勺子,还有两只新碗、两双新筷子。
女师傅说:“你来那天,我就去买了,这几天你一次也没用。”
她一字一句认真地说,眼神里满是真诚,我心头热浪一滚,上前接过锅,说:“谢谢您,师傅,让您费心了。”
她用新碗给我盛了大米粥,又打开蒸笼取出一个馍馍,说:“你先坐,这就好。”
我见她用自来水冲洗了锅,打开煤气灶,开始打鸡蛋,葵花油在锅里翻滚,鸡蛋在油里开花,大半碗炒鸡蛋在我面前喷香,这顿纯美、金贵的饭菜,让我吃饱了胃,吃湿了眼。
回到小屋,眼皮沉得张不开,睡意波浪似地涌上来。本打算去楼下洗衣服,可是胳膊软得端不动盆子。我就想:这人一吃饱,一住暖,就是全身生懒。考虑着小屋有暖气,温度高,洗的衣服可以尽快烘干,我就忍住疲惫端起衣服盆下了楼。楼道静悄悄,周末没有人,值班领导估计这会儿在楼上。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