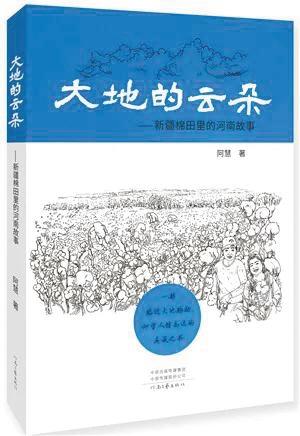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走出来,见老板两口子正忙着装瓜子。张老板撑开食品袋,月清嫂端着簸箕朝里到,食品袋和簸箕都呼啦啦地响。
月清嫂说:“炒了点瓜子你带上吃,自家种的,没打药。”
我一看,满满一袋子,五六斤的样子,就说:“那么多?我少带点儿吧月清嫂,留下给咱老乡吃。”
她硬把袋子塞给我说:“你带着吧!他们守着呢,想吃了随时炒。”
我就不再客气了。月清嫂转身到锅台,端一个塑料水瓢走过来,说:“这俩鸡蛋你带上,自家鸡子下的。这几天你也没吃好饭,俺心里怪不好受呢。”
我低头一看,红水瓢里两个鸡蛋,一颗白皮,一颗红皮。就说:“我猜你家有两只老母鸡,一只白的,一只黄的。”
月清嫂说:“你咋知道的?我养了一群鸡,就活了俩。”
我也不客气,一把抓过来,滑溜溜地烫手,看来刚出锅。
坐上张老板的半截头车,我朝月清嫂挥手告别,见她站在大门口,右胳膊习惯性地掩着嘴,看不出是哭还是笑。
我把新炒的葵花子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只暖水袋,瓜子的热气不断溢出来,满怀暖暖的香。那两个鸡蛋在衣兜里相互碰撞,热热地贴上我的皮肤。
回到六场的小屋,我转来转去,一时不知道干些什么。后来发现什么也干不了,我的心像棉丝似地被抽得老长,挂上无边的棉田,系在拾棉工老乡的身上。天气要变了,我采访的路线要变了,他们的阵地没有变,但明年、后年、大后年,他们还有机会来这里拾棉花挣钱吗?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不得不想起,路上同张立老板聊天的话题,话题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首先从棉花价格说起,这位六零年出生的老高中生,说话的腔调很像一个老乡长。
他说:“这几年种棉花不赚钱,国家收价低,一公斤只给六块钱,光拾棉工的劳务费就得支出两块钱(一公斤),再除去种子费、水费、地膜、灌带费等杂七杂八的支出,几乎不赚钱。2010年前后,那几年可是好光景,一公斤棉花能卖到十二块钱,从地里抓上来就能换成钱。现在正好减少一半的收入。”
这跟我在四场八连了解的情况很接近,但我还是很惊奇棉花的差价那么大,说:“怎么会这样?”
张老板说:“据说这几年外国进口棉比较多,价格比咱自己种出来的还便宜。咱们棉花产量也没以前高了,可能地膜对土壤有影响。那都是公家的事,单说拾棉工,我从老家把老乡们召回来,给他们买来回车票不说,还要领回家安排吃喝住,还要给他们买保险、出药钱。家里人劳累不说,最怕出事,那可就麻烦大了。说实在的,人工采棉确实好,杂质少,不破坏棉丝,能卖出好价格。纺织厂争着要,可是对国家有利,对种棉户没利啊。你想啊,机采棉一公斤才出五毛钱,是人工的四分之一,以后谁还用人工采棉啊!拾棉工慢慢的就被机械替代了。”
我想到,从场领导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就说:“采棉机可是个贵家伙,据说是从美国买来的,一台三百多万呢,能短时间普及吗?再说,这机器在几百上千亩的大块地可以顺利工作,那紧靠村庄和沟渠的小块地怎么采棉呢?不还需要人工吗?我想,若是用机械采棉,对棉花种植的要求会更高吧。”
张老板说:“没想到老乡你还挺内行,我种了那么多年棉花,这方面还没你想得深。估计团部很快要有方案出台,包括对棉花种植等各方面的要求。”
我在为棉花种植户高兴的同时,更多的忧伤来自家乡的拾棉工。我想,时代前行的脚步谁也挡不住,而衍生出的诸多问题,只有在前行中逐渐解决。
“统统交给时间吧。”我听见自己说。
回到六场,时间容不得我多想,得赶紧收拾东西。我把照相机、录音笔,还有我那生命一般的记录本,小心地装进挎包里,这挎包白天背上,夜间枕上,一天到晚没离开过我的身体,好像一离开,我就空了。
昨晚洗的衣服,薄的已经干了,厚的还湿乎乎的,我一件件叠起来,塞进行李箱。从家里带来的一大包咸菜、牛肉肠被我一点点吃完了,正好腾出地方塞瓜子,瓜子已经不热了,透过塑料袋闻见一股焦香,还有一股烟火气,像我家老奶身上的味道。忍不住抓一把,蹲在地上嗑,一嗑两瓣儿,一嚼喷香,感叹这才是真正的葵花子,在老家白吃了几十年,白制造两颗“瓜子牙”。
一时吃得忘我,直到两腿发麻。扶着床边站起来,一看,两手乌黑,去盆边洗手,镜子里照见两片乌黑的大嘴唇。
从大嘴唇里很自然地吐出一句广告词,现编的,串着新鲜的瓜子味儿:“纯天然瓜子,纯铁锅出炉,纯手工炒作。看着黑,吃着香,月清嫂牌新疆葵花子。”
突然闪现月清嫂送我瓜子时的憨模样,她满脸烟灰,满手黢黑,把刚出锅的瓜子塞进我怀里,她的目光似乎比瓜子还烫人,我被她烫得一哆嗦。
她说:“明年还来哦!”
我说:“来!你也回咱河南哦,我去火车站接你。”
她说:“中!”说完,右手背抹拉一下眼睛,那里的黑烟灰又涂加了一层。
不知什么时候我眼角潮湿了,似乎有一种亲人刚刚相认又要别离的感觉。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