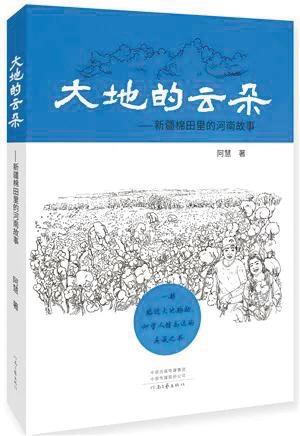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军帽女”拿手背抹一下眼睛。
我见她一只帽耳朵支棱起来了,就帮她抚平、扣好,说:“难怪你戴顶军帽子,真像一个军人哪!保护留守女童的女兵。”
她忍不住笑出了声:“哪是啊,姐!这帽子是前些天在沟里拾到的,老乡们还吓唬我,说是死人的棉帽子,我说,管它是人是鬼的,戴我头上就是我的,暖和不冻头都中!”
我的头皮直发紧,冷风钻进毛线帽子里,挨个去薅我头发。我用手捂了捂,风又来舔我手背。我懊恼地说:“忘记戴手套了。”
一扭头,见旁边棉垄一姐儿们,裸着双手拾棉花。
我咣啷咣啷蹚过去,说:“啊,你也忘记戴手套啊!”
她在口罩下粗声大气地说:“有手套也不能戴。”
突然一下想起来,四场八连的那位大姐说过,有雪有霜的时候,最好不要戴着厚手套拾棉花,手套容易湿,手指更容易患风湿。她夸我说:“你这妹子,比俺这老花工还懂哩。”
确认她的确比我年长后,我谦虚地说:“大姐,我这是鹦鹉学舌——现学现卖。”
寒气是群小怪物,从地皮上直朝我大衣筒子里钻,我赶紧蹲进了棉花棵,一点点挪着走,活像舞台上的武大郎。
终于靠近大姐了,见她披了件花布单,看得出是块包袱皮,绿叶红花很惹眼。我听见她勾头笑,那笑声挤在喉咙里很古怪,背上的红色月季花一颤一颤想绽开。
我说:“大姐是在笑话我,我这人赖毛病多,怕热又怕冷,啥活儿也干不动,没有一点儿用。”
她又笑了,说:“妹子你这是富贵病,不像我,天生的劳作命。”
大姐屁股底下垫着鼓囊囊的棉花包,她是坐着拾棉花,那股自在劲儿,活像坐在自家的大堂屋。她那双辨不出颜色的手,像两个铁耙子,唰唰唰,不断地将棉朵搂进腰间的棉包里,腰间塞满了,她就站起来提一提、礅一礅,双腿一跨,又坐在了棉包上。棉包皮也没沾上泥,育苗时的白地膜把泥土糊得严严的,膜上的碎雪,被大姐用脚轻轻一抹就干净了。
我说:“姐呀,这包里棉花带着雪,你坐在上面不凉吗?”
她翻眼看看我,说:“棉花吸水啊,棉朵上那一撮儿雪,还不够棉丝吸的哩!有点潮,不会湿。”
她凑到我耳根上说:“可压秤哩!虽说冷点儿,受点儿罪,可比那大太阳顶头晒的时候,要多挣几十块钱哩。每年在这天气里抢收棉花,老板还另加钱哩。弄好了,能多挣一张老头票!”
她眼睛左右一扫说:“要不是这,她们能乐意下地呀!虽说这时候拾花冻手,可谁也不嫌钱烧手。我说的可对?”
我小鸡啄米似地点头说:“姐说得对!我还以为是老板撵你们下地哩,老板过称时不除水吗?”
大姐说:“不除!老板吃点儿亏也愿意。你想啊,要是一连几天下大雪,这一地的棉花烂地里,他可真是亏大啦!要是我,能心疼死。”
我问:“大姐家有几亩地?”
她说:“别提地,提地我会眼气死。”
二十二朵花
“土地姐”刘三请
刘三请 ,女,五十六岁。生有一儿一女,儿子三十二岁,已婚,大学本科毕业,在西安成家立业;女儿二十八岁,已婚,职专毕业,嫁到郑州,做服装批发生意。老伴五年前病逝。
望着记录本上的文字,我说:“刘姐,你儿女都这么有出息,你不会缺这俩钱花,怎么也来这儿受累呢?”
她一摆头说:“我就是个穷命头,说了你也不会信。”
“三请这名字是俺爷给起的,我前头有俩姐,大姐叫大请,二姐叫二请,轮到我这就叫三请。上小学报名时,知青老师把我名字写成了刘三顷,他说,三顷就是三百亩地,比那个‘请’字有豪气。俺爷一看吓坏了,因为俺家是地主,正好置办过三百亩地,赶紧又改回了老名字。哎,也别说,长大后我就是喜欢庄稼地,见地亲哩很。俺四口人分了三亩地,闺女是偷生的,没有她的地。我见天儿都在地里滚,三天不下地,就肉酸、皮紧、骨头硬。到地里,抡开膀子干一通,锄草、锛地、撒化肥,浑身舒坦得不得了。三十岁前,我没尝过药啥味儿,肚疼、头晕、发大烧,到地里干上一天活儿,啥病都跑得没影了。生俺大孩儿那天,我在地里割豆子,肚子一疼,扔下镰刀往家跑,路上遇见个赶牛人,他拍着牛屁股说,‘肚子疼,往家跑,不生闺女就生小儿。’我哪有心思搭理他,憋着一口气跑到家,呼啦一下,孩子就落地了。俺老伴活着时,没少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块大坷垃,你就是棵蜀黍苗,你就是根毛毛草,离开土地不能活!’”
“土地姐”刘三请,学着她老伴的动作,边说边笑边用指头点着我。
我迷蒙地看着她,脑子里一阵乱想:这世上有写书上瘾的人,比如作家;有打牌上瘾的人,比如赌徒;有喝酒上瘾的人,比如酒鬼。没想到,还有种地上瘾的人,比如这姐。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