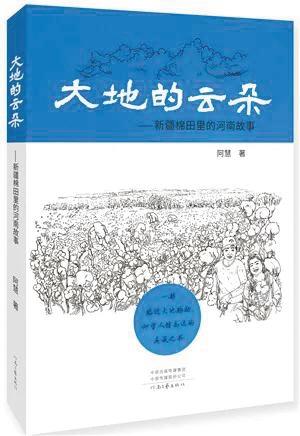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我摸摸丫丫身上的小薄袄,担心她会冷。任叔说:“打小冻习惯了,不害冷。”
我看那蘑菇长相有点丑,任叔说,这是树林中里长的野蘑菇。
进了大堂屋,暖气让我很受用。说实话,早在集市上我就冻得受不住了,一开始是皮肉哆嗦,没多会儿心肺一起哆嗦,像有人在腔子里提着来回甩,甩得我摇摇晃晃站不住。我在沙发上坐下,背靠一组暖气片,热气从里面传出来,源源不断的暖。这大屋沿墙壁安装六七个暖气片,一个小型的炭火炉把屋子烧得热热的,把这个冬天烤得暖暖的。我微笑着伸伸腰,像一只按着四蹄拉长身子的老猫。
阿姨从厨房走出来,两手湿淋淋,她黄瘦的脸上始终布满笑,好像她从没为什么事犯过愁。她笑吟吟地问:“慧回来啦?”
随阿姨进了里间的厨房,空间不大,却安置了两个铁炉灶,红红黄黄的炭火扑包水壶的大屁股,烫得它吱吱叫。两条二尺来长的大草鱼,平躺在大洗衣盆里,亮起丰厚的白肚皮,两头翘出盆沿,看样子,它们躺得不怎么舒服。我刚在盆边蹲下,正赶上一条鱼伸懒腰,扑棱一下,一个精彩地打挺,溅了我和姨一头一脸的黏腥。
阿姨说:“你看看你看看,它有多大劲儿,怪不得咱老家人叫它‘混子’。”
她顺力把大混子拨拉到脚旁的案板上,说:“这是二娃子两口一大早送来的,开车从人家渔场现捞的。趁花工都在家,你来家也没吃上啥,今儿个咱炸鱼,喝鱼汤,改善改善生活。”
阿姨抹掉额头上的一片鱼鳞说:“其实俺们接长不短地改善生活。”
菜刀落在鱼身上,阿姨斜着刀刃刮鱼鳞,嚓嚓两刀,那鱼腾地竖起来,尾巴支住盆底子,大嘴朝天吼,我没听见它吼声,但看见它亲自站起来,个头儿几乎和我蹲着一样高。正惊诧,它“呼通”一声躺下了。
阿姨惊魂未定地看着鱼,惊呼:“天爷啊,看疼哩!看抖哩!罪过罪过,我叫你受苦了!”
她拿眼睛望着我,眼神像个犯错的小孩子,阿姨说:“光顾着给你说话哩,咋忘了先拍死它了?看弄的啥事,天爷吔!”
在阿姨没拍到鱼头之前,我抱着头先跑了,一蹦子跑到院子里,直到一丝鱼腥闻不见。
整个下午没见太阳,也没见拾棉工姐妹出屋,我溜出来在她们门口溜了两趟,没听见啥动静,知道她们在歇身子补瞌睡,就轻手轻脚地退回了。独自出了大门,站上通往水塔房的水泥路,见五六只肥硕的大母鸡懒散地站在路面上,叽叽咕咕地说鸡话。说它们大,我可绝对没有夸张,它们头大,爪大,身子大,一只至少十五斤。红黄的羽毛,自己会发光。母鸡们一走一探脖儿,一步一晃悠,两步一停歇,三步一抖擞。那架势,活像宫殿里的娘娘们出游;那做派,又高傲又散漫,还矜持得让人受不了。
我一看见这群瓷实实的母鸡,肠胃就开始受不了。不知怎么地,就幻想出它们在炒锅里的种种模样,那淳厚的汤柱高高低低,咕咕嘟嘟,那鸡肉的酥香起起伏伏,稀里哗啦。我的幻想越来越不像话,只好张开臂膀赶鸡走,它们依旧从容踱步,鸡眼直视。只好我走,毅然弃鸡而去。
走到两棵大树下,仰脸看,却辨不出是什么树。树干直溜,别的树已成斑秃,或全秃,它俩却一头青丝,简直是枝繁叶茂,还挂着点点绿果。这有点儿气人,我跳着脚拽它们的枝条,直到跳不动了,也没能动得它们一根毫毛。
刚回到院子里,任叔抱着丫丫回来了,丫丫手里一簇青枝绿叶。我一看,就说:“是那两棵树,叫什么名字?”
任叔说:“沙枣树。”
他从丫丫手中抽出一枝递给我,柳枝儿似的叶片间,藏着两粒小青枣儿,似两枚青玉耳坠。
晚饭后走进土坯房,挑开棉帘,见里面昏暗一片,一个小灯泡散发有限的光。小屋空间不小,两排搭起的长铺,中间留有走道,靠里的窗户下放一张长木桌,一个女子在照镜子梳头。
我含着浓浓的情感说:“姐妹们好哇!”
几个躺在被窝的人没有动,也没有搭腔。侧歪在被垛上的两姐妹翻身下床,一个说:“哎呦,大姐来了,刚才我还想到你,以为你还在睡觉哩。”
张粉花拉上我的手,汪兰兰拍着床边让坐下,我示意她们小声点儿,铺上的姐妹陆续欠起身子说:“不碍事,俺都没睡着,睡了一下午这会儿不困了。”
我朝她们看过去,说:“一听话音儿就是咱周口人,在这见面亲哩很。”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