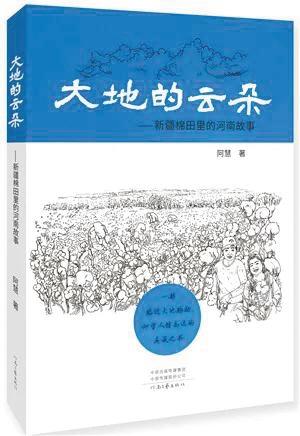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啥?”张粉花忍不住了,嘴巴凑到江水莲脸上说,“你不是个人吗姐?你不会抱上孩子跑吗?还在那等着挨死打?”
“家暴女”江水莲说:“我没想到跑,也不知道往哪儿跑。要是被梅家人追上了,抢走俺儿子,我还咋活哩!我放不下俺孩儿,舍不得我种的庄稼,还有这个家。”
我一时无语,只能无语。
张粉花缩回脑袋,坐直身子说:“活该你受罪!”
江水莲说:“受就受吧,生来受罪的命。那时候,一个心眼盼着俺儿子能长大,能像他爹疼他奶一样心疼我。谁知这孩子从上小学起,就不正眼儿瞧我,嫌我黑丑,窝囊,站不到人前去。上大学回来,他给我说话的口气就像呵斥一条狗。我忍了,一个人在暗影里打哆嗦。心说,只要他没病没灾就好,只要他平平安安就好。儿子梅栋是三代单传,婆婆说,‘俺栋栋是十八亩田里一根苗,主贵着哩。’俺见儿子一天天长得又嫩又俊,跟杨树苗一样,心里那个甘甜啊。儿媳妇娶进门,我还没有摆起做婆婆的架子,新媳妇就耍起威风来了。她翘起指头说,‘我可不是刷锅烧灶的人,家务活儿谁想干谁干,我可不干!’她不干我干,进家都是神,我是敬神的。我一天到晚心里发慌,恐怕惹了老的,恼了小的,连口大气儿也不敢出。年节里,我一个人锅上锅下地忙乎,菜一上桌,老老少少都吃开了,没有人记得还有个我,还有我这头没有卸磨的老驴。我倚着门框,捶自个儿的老腰,歪鼻子又酸又疼。这两年俺老了,儿孙们也不用俺管了,牵挂也少了,我想的事也多了。夜里睡不着就对俺娘说,‘娘啊,这人心咋恁深哩?咋恁凉哩?一家人都摸不透、暖不热。我把心砸碎了、熬成渣,一点点喂他们,他们咋就不知饥饱哩?品不出甘苦哩?’天亮了,我想走,去哪儿哩?去哪儿都中,只要离开家就中,只要叫梅家老少看不见我就中。我就报名来新疆了,俺男人说,‘不伺候俺娘,还捶你!’他都六十多的人了,还有这狼心。我一句话也不说,硬着眼珠子瞪他,他放下拳头蹲在了床脚。那一会儿,我觉得他也是个可怜的人。”
江水莲很响地吸溜一下鼻子,好像这才感觉到鼻孔在顺畅地通气。这个善良到无法再善良的女人,一生都在为爱妥协、退让,一尺尺,一分分,一寸寸,只退到无路可退,只爱到无爱可爱。最终,她选择了爱自己。
“家暴女”江水莲孩子似地说:“俺抓俩钱回家,先到集上给自己买一件红鸭绒袄穿。成亲那天穿的棉袄,是俺大姐手工做的,胖胖大大的可难看。”我想像着水莲姐穿上新红袄时的样子,两鬓的白发如棉丝,侧歪的鼻梁很俏皮,黑油的老脸有点红。她老伴看后有什么反应呢?不去想他,一个不值得去想的愚忠愚孝的可怜虫。
股股冷风不断从棉布帘与门框缝隙钻进来,泥屋的温度越来越低。我抱紧膀子坐着,门后大铺上的一个姐妹伸手把棉帘拉严实了,依旧坐回被窝,两手踹进袖子里,面带笑容望着我。她原来一直在听我们说话,一个人靠在墙角,光笑,不语。
我冲她一笑,说:“谢谢你妹妹,这样暖和多了。”
她依旧浅笑,说:“呢是个啥事了!”
我没听懂,迷茫地看旁边的姐妹们。张粉花哈哈笑着说:“她是说,‘哪算个啥事!’山西话。”
“噢!”我远远地问说,“你是山西人?”
她笑着点头说:“嗯哪。”
我一时来了兴趣,走到她床铺前,说:“妹妹叫什么名字?一个人来新疆吗?”
二十九朵花
“互助女”张小彩
张小彩,女,三十九岁,山西农村人。生育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十六岁,念高中一年级。丈夫四十二岁,四年前患脊柱侧歪,手术两次,无性,无劳动能力,在家留守。她的“互助”男友,河南周口农村人。
张小彩圆脸大眼,肉肉的鼻头,下嘴唇一道天然黛色唇线,看上去更有立体的美感。
我说:“山西出美女,小彩妹妹很好看。”
她轻咬下唇说:“哪儿呀,我丑哇。”
我说:“你会说普通话?还挺标准的嘛。”
张粉花走过来说:“她还会说咱河南话哩。”她朝小彩飞了个有内容的眼神说:“对吧小彩?”
看来姐妹们对小彩的情况挺了解,她们波澜不惊的样子,让我有些吃惊。
我问:“你家爱人生活能自理吗?”
她轻言慢语地说:“他前年第二次手术后,能下床走路了,腰板直不起,走不出院子,出不了山,只能在家做顿饭。今年双胞胎娃娃考上镇高中了,住校不回家,他一个人在家轻松些。我来新疆打工三年了,春天来,腊月走。种苗、摘瓜、打葫芦什么活儿都干过,棉花季结束后,我就进城里饭店打工,有时在棉花场打杂。在城边租房住,有时几个人租一间。我一挣到钱就打给我女儿,让她转给她爸爸。我识字少,不会打钱,邻居吕梁帮助我,他是你们河南人,来新疆打工七八年了,在工地上拉电线、装电灯。他的婆姨跟人跑了,一个女娃五岁了,在周口奶奶家养着。吕梁每个月都骑着摩托带我去打钱,有一次,我两个月没有发工钱,娃他爸没药吃,两个娃娃没饭吃,我站在门口急得哭。吕梁把他身上的钱全掏给我了,骑摩托连夜到市区去打钱。回来时刮着大风,还下着大雪,吕梁让我钻进他的大衣里,我搂着他的后腰,闻到他身上的味道,被他热烘烘地暖着,幸福得差点儿晕过去。到家时,吕梁冻得下不来车。我给他做了一锅香辣刀削面,把吕梁吃哭了,我也哭了,外边下着雪,我们在屋里傻不叽叽地哭了大半夜。后来我就搬到他屋住了,我省了房租,他省了生活费,我把节省的钱打回家。他以前穿得邋里邋遢的,我一天天把他打扮得展展挂挂。有时候,我感到心愧,觉得对不起娃他爸。几次想和吕梁分手,可是感情上分不开,我很待见他。身边不少打工的也这样,临时搭伙过日子,还是各养各的娃,各顾各的家。”
张粉花说:“俺听说这叫‘互助’,俺村里在广东深圳打工的人也‘互助’过,回村后他们互相说。家里人知道了,有的找对方打一架,有的索要几个钱儿,有的不哼不哈过去了,也有个别离婚的。”
我问小彩:“你丈夫知道吗?”
她眼里漫起一层泪水,说:“他可能怀疑到了,我回家他也不问,无奈吧。”
张小彩无奈地摇摇头,几滴泪珠溅下来,有一滴落在我记录本上,“噗”地一声闷响。
我望着她,心隐隐地疼。
我说:“这样不行小彩,还是分开吧,趁他还没谈女朋友,趁悲剧还没有来。”
我不敢待在泥屋了,掀开棉帘钻出门。小彩的哭声洪水般不可遏制地冲出来,冲得我的脚步磕磕绊绊、歪歪跩跩。
我走进厨房,见阿姨坐在盆边洗衣服,衣服和水冒着烟。我看出盆里花花绿绿小孩的衣服,知道都是丫丫的,就撸起袖子说:“阿姨我来洗,你歇着。”阿姨也不外气,站起身给我腾地方,像对待自家的亲闺女。她一边往小锅炉里填煤炭,一边说:“慧啊,今晚我熬小米粥,你过来喝吧。”我用力地搓衣服,说:“好的阿姨,我好些天没有喝热粥了,小米粥更想喝。”
我朝门口看了看说:“刚才那女子是谁呀?我听见她叫你姑。”阿姨“哦”了一声说:“你说杨敏啊,我娘家侄媳妇,她年年来家帮我拾棉花。”我说:“人长得不错,就是一脸愁容。”阿姨回头看看我,没说话,又往炉膛里加了两块炭。
我在院里铁丝上晾衣服,见任叔扯着丫丫往大门口走。我擦干手追上去,问:“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任叔站下说:“带丫丫到果园玩。”
我也想看新疆的果园长啥样,便跟上一起出了门。
向北走上一段路,路西一片树林子,我初来那晚看见过,却没想到是任叔家的果园子。我们在园子边站下,落叶的果树密密实实。任叔说:“这是你弟弟妹妹们开的荒,种的有桃树、苹果树,十来亩地呢。”
我说,我只见了大娃和二娃。任叔说,还有大妞二妞和三娃,丫丫的爸爸是三娃子。
果园里的土地湿黏黏的,雪刚化过,无法往里走。丫丫采了一朵大蘑菇,高举着让她爷爷看。任叔说,雨雪过后,蘑菇快速生长,果树下最多。想起那天任叔采摘的野蘑菇,我俯身满地找,任叔指给我说,蘑菇一般长在倒伏的树干上,还有腐烂的树根上。果然,一个圆盘似的树桩隐在湿潮的枯草中,旁边生出一窝小蘑菇,像拱出地面的小白兔,嫩呱呱、肉乎乎,顶上圆嘟嘟,我兴奋地采了一大把,任叔敞开塑料袋装进去,说:“还好,没有采到有毒的。”
“还有毒蘑菇?”我吓了一跳。
任叔说:“你看这边几朵大的就有毒,吃了呕吐泄肚子。”我看它们生得挺好看,个个高高挑挑,细皮白肉,像把小白伞似的。难怪呢,越好看的东西越危险。
站在路边,任叔指着房屋让我看,果然发现,远近几座主房都面朝东方,稍微偏南,不是坐北朝南中规中矩的那种房。任叔说,四十年前他逃来新疆时,也觉得这里的房屋走向很奇特,后来才知道,东方是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人们唱着《东方红》把房屋盖向东方,在当时是有重大意义的。
任叔说:“有一个从口上(内地)来的年轻人,他盖了一排坐北朝南的新房子,谁看谁别扭,都说他的房屋盖歪了。好比一张桌上十人吃饭,九个左撇子,一人用右手,正确使筷子的这个人,反而被认为不正常了。”
“有意思,”我说,“任叔不愧是老三届高中生,语言表达那么好。您也是早年移民新疆的吗?”
他摸了摸额头说:“不是,最初是盲流。”
三十朵花
“盲流叔”任二超
任二超,男,六十二岁,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六户地二道渠子人,原籍河南周口农村,20世纪70年代初到新疆谋生活。生育三子两女,皆在新疆成家立业,任二超成为本地植棉大户,受到当地政府嘉奖。
第一节
沙发前的茶桌上,两杯茶水静静地消耗着热度。我面朝任叔恭敬地坐着,急切地摇动手中的笔杆,记录本上的直线横格,似一垄垄精心修整的棉花畦,引领我种下一棵棵小棉苗。当我一字字记下任叔叔的口述时,我和他都没有想到,在余下的四天里,我的笔录,会不间歇地填满上千行横格,记下两万多有呼吸的文字。
这是我和任叔都没有想到的。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