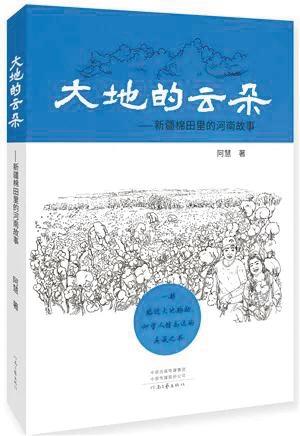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任叔刚在沙发上坐稳,就说:“其实我不姓任,因为我家老太爷不姓任。关于家族血脉,百十年来族人们从不提及,我爷爷奶奶没有说过,我爹娘在世时也没有说过,可是任家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我们这一支是河北回民马家的后人。”
我吃惊地望着任叔,他的右手在头顶缓缓抚过,花白的寸发在瞬间的倒伏中纷纷复原,犹如苍茫岁月的起伏。
他说:“我爷爷叫任安,大爷爷叫任套,可是村里人却喊他们马套,马鞍子,我和大哥小时候也听见过几回。有一回,我无意中听到爹娘的谈话,俺爹说,那天他睡在俺爷奶的脚头边,村里人给他们开玩笑,趴在窗外喊,‘官兵来抓恁啦!’爷奶慌忙往外看,吓得连鞋都找不着。我一来二去明白了,俺老太爷是捻军的一个小头头,人高马大,练就一身好拳脚。起义失败后,官兵一路追杀,俺太爷骑马跑,怀里搂着俩儿子,后面坐着俺太奶。四口人一气儿跑到黄河边,俺太奶回头一看,大队的官兵快要追上来了,她翻身滚下马,大喊,‘快跑啊!’俺太爷勒马转回来,见俺太奶掏出剪刀猛扎自己的脖颈子,血柱子喷到马腿上。这时候,官兵的马队追来了,河道上的尘土飞起来,有树梢子那么高。俺太爷趁机裹紧俺爷爷和大爷爷,一头扎进黄河里。”
我端起茶杯,猛喝两口水压压惊,那情景就像在脑子里过电影。
任叔叔不喝水,他接着说:“他爷儿仨喝了一肚子黄河水,被人救上羊皮筏子时,发现还会喘气哩。就这样逃到河南任家庄,俺太爷觉得安全了,就待在村里不走了,住进村头的草庵子。村里有一对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生孩子,村人见俺太爷拉巴两个小娃子不容易,提议让他入赘。俺太爷本名叫马喜,老夫妻给改成了任国喜,随了任家的国字辈。从此,俺这一支就姓任了。”
阿姨提着个热水壶,给我们的杯子续满水,她笑着对任叔说:“当初媒人婆也给俺说过恁姓马,不姓任,我说,管他是马还是人,我愿意嫁他就中了。媒人还说,他家是黑五类,我说,我还富农哩,正好门当户对。”
我跟阿姨一起笑起来。我说:“咱仨是黑五类开会,俺家原先是地主成分。”
任叔说:“提起这,我心里还是打哆嗦。不是因为俺爹,我还来不了新疆哩。”
“这里边有故事?”我端起茶杯。
任叔小心地抿了几口茶,他说:“俺爹叫任甫,当过兵,能写会算,在国民党的部队搞军需,俺娘也从老家接部队去了。娘活着时说,‘游击队的陈同志和赵同志,隔长不短地来咱家,他俩也是河南人,喜欢吃我擀的面条。恁爹给游击队弄过几回药和枪,有一回还装成逮鱼的,划着船把东西送到黄河边的芦苇棵里。’后来俺爹怕暴露了,偷跑回老家种地了,一直到1955年冬天全国肃清。”
他放下茶杯说:“那天我和俺哥在奶奶里屋睡,半夜听见有人哭,哭声很吓人,像被人扎了一刀子。我往俺奶怀里钻,俺哥说是娘在哭,跑到西屋一看,俺娘大着肚子披头散发坐在地上哭,手里抓着俺爹的破夹袄。俺哥说,‘咱爹叫人抓走了。’我问谁抓的,他说不知道。后来俺爹回忆说,那晚来人跳墙而入,个个蒙面,喊一声他的大名,蒙上脸捆起来就走。俺爹以为遇上绑票的乱匪了,出村二里地,他听见风吹芦苇棵子响,估摸是到乱坟岗子了,就说,‘好汉,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恁要杀就把我杀在这儿吧,村里人听见枪响,能给我收尸,就地埋葬,别被野狗撕吃了。有人说,‘没人要你的命,我们是政府的人。’俺爹一听明白了,他是被人诬陷了。从此俺爹离家了,被判了十五年,在青海戈壁滩劳改。俺爹被抓时,俺哥十岁,我七岁,妹妹四岁,俺弟弟还在娘的肚子里,两个月后才出生。1959年吃食堂,四岁的弟弟坐在地上端着小碗喝汤,俺娘俺奶奶碗里一寸长的面条都挑给他吃了,我和俺哥不舍得吃碗底上的几个面疙瘩,也跑过来倒给弟弟。他两腿瓤拉拉,不会走,坐在地上,肚子鼓鼓的挨着地皮,连小鸡鸡都盖住了。肚皮像一层薄纸,透明似亮的,能看见里面的菜梗子。”
任叔嘴唇颤抖,他张开右手掌说:“俺弟弟现在身高也不足一米五,外号大个子,五十多了没娶上个女人。但他性格倔强,是个大男人。1972年,我和弟弟一起来新疆找俺哥,现在弟兄仨都在这儿,妹妹也嫁到新疆了,1974年我们也把爹娘接来了。”
“您家老父亲平反了吗?”我仍牵挂着这件事。
任叔摇摇头说:“来新疆时还没有,但他在青海劳改场被提前释放了。1962年的一天,俺爹正在山上砸石头,两个人骑着大马走过来,递给他一个盖红章的公函。”
这时阿姨把两盘菜放桌上,说:“别光顾着听恁任叔说,饭菜快凉了,赶紧吃吧。”
我不好意思地合上记录本,朝门外看看,天不知什么时候黑下了。丫丫跟随阿姨从艾巧屋跑回来,任叔一把抱住她放在腿上。他有一阵子没注意到丫丫了,连她什么时候睡醒的都不知道。
阿姨麻利地摆好碗筷。这些餐具好熟悉,我认出是艾巧屋里的,我从家里带来的小碗摆在那儿,稠稠的小米粥冒香气。阿姨指着盘子说:“尝尝这盘辣椒炒蘑菇,这蘑菇还有你采下的。都是在艾巧灶上做的饭,你放心大胆地?吃啦!其实俺家干净得很,就是怕你不发不安心。”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