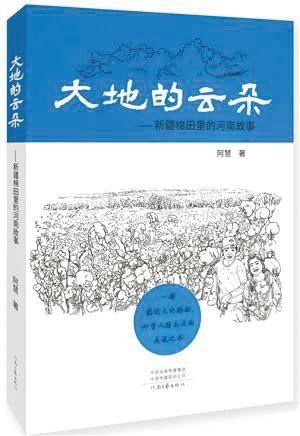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任叔说:“最苦最怕的还是‘贫专队’。”
我不解地问:“啥叫‘贫专队’?”
任叔说:“当时的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贫宣队’,‘贫专队’大概就是贫下中农专政监管队。‘贫专队’的人员,骑大马、戴袖章,一支马队五六个人,专抓没户口、没证明信的盲流。我被他们抓过一回,我现在讲的是第二回。春天一过,积雪化了,‘贫专队’的马跑得更快了。白天好躲,晚上我不敢睡屋里,天天睡房顶,再冷也不回屋,好提早逃跑。那天,我听见大妞哭得很厉害,就下来看看。没想到马队就到了,把我摁地上,麻绳一捆就栓走了……”
这时里屋一声小孩哭,我还沉在故事里没出来,以为是大妞。丫丫却在屋里哭着喊:“任二超,任二超。”
我一看手机凌晨3点了,“呀”了一声站起来,任叔早已去哄丫丫了,似乎比当盲流时跑得还要快。
我躺在小床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却火车隆隆。那豆虫般的绿火车,在越来越荒寂的大山里剧烈蠕动,它接连吐着墨汁似的浓烟,不断发出鸣叫。荒原里雾气蒸腾,隐现年轻的身影,随风飘动的破布衫,倔强而青葱的面孔,火烧云烧透了的天空,马蹄踏碎的金盏花,仓皇逃走的脚步,撕碎空气的喘息,婴儿惊愕地啼哭……
第三节
今天的早晨是从上午开始的。
我伸个懒猫式的懒腰,听见窗外有动静,透过玻璃看到,二娃子两口正挥舞铁锨刨菜地。两个年轻人齐头并进,听不见铁锨插进泥土的声音,但见他们劳动的姿态生动可人,面前翻出的新土黑湿一片。
哦,原来这房后还有一片大菜园,新疆的土地那么多,任家老少却爱惜地打理出一片又一片。骨子里的河南人,骨髓里的土地情结。
走出屋子时,阳光像关闭已久的金毛大狮子,一下扑到我身上。没想到雪后的太阳会这么生猛,我呆在院里拿双手捂眼睛,从指缝里瞄见了院前菜园的人影。阿姨一手拿小铁铲,一手举着一棵大白菜,朝我走过来。白菜被她剥去冻坏了的老叶,它就扑散着清白的大叶子,在我的眼前开着素净的花。我上前揪下一片白菜叶,不由分说放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起来。味蕾开了花,清爽得没法说。阿姨惊讶得嘴巴合不拢,她拿白菜戳了我一下,说:“这闺女,生吃啊!这不洗不涮的能入口吗?”
我喜眯眯地又伸手,她麻溜地把白菜藏身后,说:“上午吃,白菜炖豆腐。”
任叔在那边说:“薅个萝卜吃吧,霜雪打后,萝卜脆甜脆甜的。”
我走过去,见任叔挥舞铁锨,已经翻好了很长一垄地。我刚挨近地边,小风送了一股新鲜的土腥味。我说:“没想到雪后的土地干得那么快,要是咱老家的淤泥地,会湿黏得刨不动。”
任叔边刨边说:“那是,这里土地干,前日的小雪只是给地湿湿皮儿,没洇到土层去。风一刮,太阳一晃,这地就干啦!”
我望了望土坯房说:“她们都下地拾花啦?地里可以进人啦?”
任叔说:“是的。”我站在那里迷瞪了好一会儿,不确定是去找拾棉工,还是继续采访任叔。任叔往手掌心吐了口唾沫,使劲挖几锨,很快就到了头。他拍拍手上的土,扛上铁锨说:“回屋,叔接着给你讲。”
虽然出着太阳,但屋里还是比外面暖和。我把茶端到任叔的面前,他嘬了一口说:“昨天让你见笑了。细想想,自从我爹娘去世后,我多年没这么掉泪了。闺女你一来一问,我把沉到地底下的老事儿都翻出来了,就跟翻菜地一个样儿。”
他放下茶杯,说:“我被‘贫专队’绑出了门,黑影里还有一帮捆着的人。我们十几人,前头一个女的很年轻,也是被反手捆着,疼得她小声哭。我明白她是一个姑娘家闯新疆,没有男人可依靠。有家的女人孩子不被抓,把男人抓走遣送回去,妇女孩子就跟着就走了。看押我们的人里头,有一个我认识,他偷偷给我松了绑,两手在前头捆绑着少受疼。我说,‘也给那女子松松绑吧!有情一块儿补。’那女子也改换到前面捆住手,一路上没再听到她的哭声。”
“我们被押进了县收容所,四处一看,高墙大院,四个墙角盖四个小岗楼,高得很。我们住进筒子房,睡大铺,人一个挨一个。关进去头三天没让干活,吃的是玉米面发糕,没菜也没粥,噎得翻白眼,就这晚上还不给吃,一天两顿饭。第三天早饭后,一个带班的小矮个儿站在院子里喊人出去干活,见我个子高、块头大,就把我给喊上了。20个人被带进拖拉机厂,安排我们除草、扫地、清理垃圾。我干活不惜力、不耍奸,带队的人第二天又点名让我去了。这一回,我存了个心眼儿。昨天我就踅摸到了,拖拉机厂院墙不高,也没有岗楼,除草棵子时,我瞄见墙角掉了几块砖。我刻意没砍那棵树,留着它遮蔽豁口。我们一猛劲儿干到快中午,日头的热度上来了,饿劲儿、乏劲儿也上来了,监管的人坐在棚子里。这个时候我跑了,两手一摁墙砖,一纵身子,一下翻过去了。前头是条大街,我往人多的地方跑。这时,我听见身后喊:‘抓盲流啊!’‘别让他跑了!’这么一喊,街上的人纷纷躲开,给我让出一条大宽路。我跑得更快了,跟一匹疯马一样。这时街边有人喊,‘跑我家来!’我刹住脚,那人伸手把我推进身后的临街门,随后把门关上了。他仍旧站在门外边,我听见马队朝前跑了。那人领我进了后院的屋子里,问我在里边几天了,我说3天了。他赶紧撸袖子给我做饭吃。记不清他做的啥饭了,光知道很好吃,我吃了两大碗。随后,我问恩人的大名。他说,‘我叫陈国平,江苏海门人。’我说,‘我叫任二超,是个盲流。’陈大哥1958年来到新疆玛纳斯县,属于上海支边青年,如今住在县城里。他一米八多的个子,身架子又宽又大,看上去比我还猛壮。这时,他老婆领着3个闺女回来了。天黑透了,陈大哥把我送到城外的漠河渠桥边,他转身回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出口。我是盲流,分文没有,人家跟我无亲无故,却这么出手相救,我无论说啥都显得贫乏。站在桥上,我把恩人的姓名和住处,牢牢实实记下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