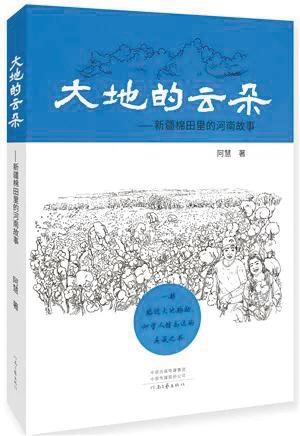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家里人可急坏了。”任叔说,“我大哥听说我被抓,去收容所找我。一问,对方说,‘任二超跑啦,八匹马都没撵上他。’我大哥一听高兴了,背着包袱回来了。当晚我就摸回了家,有了经验和教训,再也没被抓到过。 ”
任叔的表情松弛了许多,说:“生了大妞后有家有口的,我打算盖所新房子。我去河坎上打芦苇,脱土坯,跑兵团砍树。树干扛不动,就滚到水渠里,顺水拉着走。几间新房终于站起来了,我和家人差点儿累趴下。不管怎样,总算有个立身的地方了。1975年阴历七月,大娃子出生了,一家四口的户口都报上了。当时,一口人给了三分自留地,我们四口人共一亩二分地。我有自己的地了,也成了一名社员,跟大家伙儿一起下地割麦子、掰苞米、砍高粱。我干活又麻利又猛张,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不怕苦不怕累,就是怕低人一等,不被人当人看。那阵子,我感觉自己是个人了。到秋后,全家分了‘人头粮’,基本上够吃,最重要的是不被‘贫专队’抓。我这才安稳了一颗心,盲流的日子结束了。有房子有家有地种,我们哥仨一商量,回老家把爹娘和妹妹接过来,一家人在新疆团聚了。我爹那晚高兴得睡不着,在这儿没人清楚他的身份,老人家心里舒缓了。”
第四节
“还记得那个叫任水流的人么?”任叔突然问我。
我想了想,说:“同你家大哥一起逃来的四人之一吧。”
任叔点点头。他说:“我一落上户口,就被生产队重用了。社员们选我当青年排排长,当时生产队分有壮年排、妇女排。一个拖拉机大齿轮,钢做的,挂在我家的大树上,我一敲当当响。我带领青年排下地劳动,记工分、分派活儿。任水流当时受我管,我指派他干啥他干啥。时间一长,他就有些不情愿。我爱读书看报,爱在种庄稼上动脑筋。新疆的气候、光照、降水,包括种地的时令,庄稼的习性,我都摸得透,弄得懂。这六户地二道渠子,之前种过小麦、玉米、高粱、油葵、甜菜,却从没有种棉花的历史。我看水沟那边的农八师棉花种得不赖,就对生产队长说‘咱也种棉花,准成。’队长说,‘别看隔条沟,水土就不同,恐怕种不成。’我回去跟队员们一说,他们都信任我,当年我们队就改种了棉花,收成挺好。你阿姨把三亩多的自留地也种上棉花了,白棉花开得往下流。队长说,这棉花收成了,没处加工也不成啊!不加工的籽棉卖不掉。我就骑着自行车找到一个加工厂,给厂长做月子的老婆送一桶鸡蛋,给办公室主任送一袋大米,结果很快就把籽棉加工成皮棉了。当时棉花紧俏,玛纳斯棉麻公司说有多少要多少。那年,我们生产队的收入大大提高。三年前,镇上一个记者来采访,听说我种棉花的事情后,他说,‘老伯啊,你是咱玛纳斯镇种棉第一人。’”
我惊叹一声,说:“任叔您真是敢想敢干!”
“任水流可不这么说。”任叔说,“那天我当了壮年排排长,他对我说,‘看你任二超怪能耐,可跟我没法比啊。我任水流八代贫农,从我这辈起向上数到清朝,我家都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你可不一样啊,恁老爹是旧军官、劳改犯,恁家属是戴帽子的富农,你咋能跟我比哩?’我心里咯噔一声,一时认不准他是狼还是人。我们任家父子万里迢迢逃到边疆,还是没逃掉这可怕的诅咒。想到年迈的老爹,我忍住怒火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咱弟兄们比个啥?不都是给娃儿们开条路么。’这事儿过去没几天,从老家来了个放蜂的,他养的蜜蜂来采棉花蜜,那时红红黄黄的棉花朵子开得正喷。他从鄯善来我家,我和你阿姨照顾他吃住。他说,‘听的和见的就是不一样。任水流说恁家没好种,弟兄仨都孬种,任二超人凶、人赖、人厉害。’我气得双手麻,还是笑笑说,‘一人一性格,人和人看法不一样。水流哥也是苦出身,来这挣生活不容易。’那兄弟说,‘他说你坏,你说他好。一村一姓的人也不一样。’”
“第三次忍他是在我家里。”任叔说,“家里喂了鸡、牛、驴还有马。生产队里挖甜菜,剩下一小堆,不够一车拉,公家丢在田里不要了。我弟套上驴车,拉回家喂牲畜。刚刚卸到后院里,任水流追到家里,跳着脚说,‘这甜菜是我看好的,今晚上你任三超就得拉到我家去。要不送,今晚上我就叫人批斗恁爹,村里人谁不知道恁爹是反革命、劳改犯。你以为到了新疆就没人知道啦?你拉不拉?我这就去说去!’我弟气得一蹦老高要打他,被我爹在屋里喊住了。我爹摁住床说,‘装上甜菜,给他送去。’我弟孝顺,忍住气套上车,连夜给他送家了。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件事,气得我两眼直窜火。我抄起铁锨就走,被我爹一把拉住了。我爹说,‘君子怎给小人一般见识呢?这一把甜菜不值几个钱,也不是咱家种的,是公家田里长出的,咱不要了,咱给他。’我那个气啊!气他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气他往我眼睛里推石磙,气他都是同村人不该生歹心,气我怎么努力都被人看不起。我想不开,一天一夜不吃不睡,那气直往脑门上顶,眼前灰蒙蒙看不清东西,我真想一头在墙上撞死。一连半月我气难消,出门脚打飘,扶墙走。你阿姨一步不离地跟着我,怕我气死了,还怕我把任水流杀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