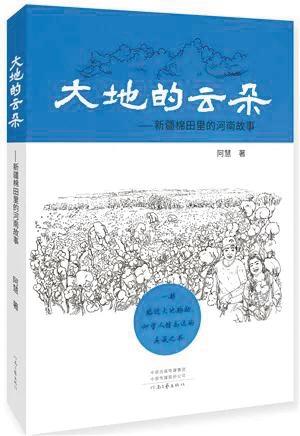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我说:“所以您成了州、县、镇劳模,年年都发大红证书。”
任叔有些惊讶,他说:“你咋知道的闺女?你阿姨说的?”
我说:“我翻看柜子里的那摞证书了,有您的‘致富带头人’‘先进工作者’,还有大娃子的‘团员致富能手’‘地膜棉花状元’。你们父子杠杠的!”我禁不住用了句流行语,还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嘿!哪能值得说?”任叔搓着大手说:“那几年真是苦得很呐!那一年我和你阿姨,苦筋巴力地种了百十亩棉地。当时,棉花生长期浇水是大事,水渠放水时,到谁地头谁开沟放水,水头错过去了就不在回来,依次浇灌前头的棉田,水不倒流。那时候,三娃子和二妞还很小,让你阿姨照顾家,我一个人赶着马车,带着干粮下地了。从天不亮一直等到半下午,人困马乏,我把马拴在空地上吃草。这个时候水来了,我飞奔去挖水道,雪山水跟一群白马一样哗哗地跑。眼看百十亩地快浇完了,突然有人喊,‘二超,你的马!’我跑过去一看,娘哎!我的马矮了大半截,四条腿陷进淤泥里,跑水啦,水把马站的地方泡塌了。马害怕呀,跟人一样,使劲儿纵身子往上拱,越拱越下陷,眼看要没了马脊梁。我当及脱下布衫子,铺在泥地上,旁边的人不断扔过来晒干的草,我边铺草边往前走,用绳索拴住马前腿,村人套上别的马使劲拉。可怜我的马,拖拖拉拉上来了,卧在那儿像一滩泥,心疼得我鼻子直发酸。”
阿姨过来提醒说:“还有一次,也是浇水。”
任叔一拍脑袋说:“是哩!那回我和你姨一起去等水,也是从天明等到天黑。点上马灯,远处响起野兽叫,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不知道是狼还是狐。野地里空旷有回音,那叫声打着卷儿,阴森森的,听起来像叫魂。夜里冷啊,寒气打脸,我和你阿姨围着被子坐在马车上,只敢一迷糊一小会儿,不敢睡,怕水到了听不见邻居喊。有时一眨巴眼,瞧见芦苇棵里有光亮,绿汪汪的,一看又没了。再一看,亮光在对面棉棵里出现了,一白一黄,一阵刷啦啦地响,消失不见了。我和你阿姨没害怕,俺俩都不迷信。只是一天没吃热乎饭,离家几十里,只好就着咸菜啃干馍吃。还不舍得吃完,留几个馍馍天亮吃。放完水,浇好地,天还黑糊着,我和你阿姨都累软塌了,拿铁锨当拐杖拄着走,胶鞋里的泥水一走一咕唧,双脚泡得没有知觉了。一步步挪到马车旁,想啃几口馍馍吃,你阿姨伸手一摸,馍馍袋子没有了。举着马灯照,地上一溜花脚印,看样子是狐狸。我俩照着脚印找到芦苇边,找见一块咸菜头。你阿姨说,‘别找啦,谁吃都一样,它也一夜没睡了。’她拾起咸菜头咔咔嚼着吃,还说,‘狐狸哎,谢谢你给我留的咸菜啊!’”
阿姨听后哈哈笑,说:“我是这样说的么?记不清楚了。想想还真有些后怕哩,这幸亏是只狐狸,只叼走了馍袋子,要是遇见几匹狼那可遭殃了,马和人都难活。”
夫妻俩轻飘飘地说着过往,我心里却凉瓦瓦、沉甸甸的。
我写下:荆棘的路难走,向上的坡难爬。棉花朵朵开,大地日月长……
还想再跩几句感伤的文字,听见阿姨说:“二儿媳妇把午饭做好了,叫二娃子回来下地送饭吧。”
任叔拍拍手,站起来说:“他办事去了,今儿我去送。”
我说:“我也去送。”
这块棉花地相当远,车轮滚了一阵子,停到了地头。一片干芦苇在我面前枯燥地响,任叔说:“这就是当年狐狸偷吃馍馍的地方。”
棉田白得四四方方。乍一看,就像把天上的云朵切下来一块,宣腾腾地平铺在棉田上,让人无端地生出,跳上去打个滚、蹦个高的想法。
拾棉工姐妹正密密地围着云朵忙,活像织女忙抽丝。我正想走向“织女们”,任叔指着一垄干涸的沟渠说:“那个姓王的小伙子,就是在这沟渠边被扭走的。”
我敏感地问:“谁呀?扭哪儿去啦?”
任叔说:“看见右前方的村庄了吗?六年前,那孩子就在那打工。”
三十一朵花
“悲剧男”王二蛋
王二蛋,男,二十七岁,河南某县农村人。自幼父母双亡,跟随爷爷长大,小学毕业。六年前,经周口表哥介绍来新疆拾棉花,后因一宗凶杀案被判死刑。
任叔三言两语的介绍,足让我的头皮发麻。
我嘴皮子有些不利索,问:“枪毙了吗?怎么回事儿?”
任叔遥望村庄说:“我也只见过那孩子两次,一次是他在沟渠那边拾棉花,一次是在法庭里,我跟着去旁听。枪决他那天我没去看,不忍心看。这些年,老人们聚在一起时还提到他,说,‘这个二蛋啊,真是个二蛋。’”
“哎!”任叔叹息一声说:“其实王二蛋长得不难看,圆头方脑,看上去憨乎乎,不精也不傻,不爱多说话。在法庭上,他就翻来覆去一句话,‘我就是想杀她,杀死他全家。’这句话送了他的命。”
“事情是这样的,”任叔回忆说:“那年,王二蛋在棉花季子结束后还没走,介绍他来的表哥也走了,他还不肯走。这源于老板娘的一句话,她说,‘二蛋呀,你回家弄啥?你爷爷也死了,家里除了老鼠没活物。我看这样吧,你拾棉花的六百块钱先存在我这,眼下就要捡地膜了,你去捡吧。冬天你帮我家放放羊,春天再帮种棉花。不白干,我按天工给你算钱。’王二蛋实诚啊,一听挺划算。家里的老房子快倒了,表哥劝他出来挣俩钱,积攒下来翻盖房子,孬好再娶个媳妇儿,这好日子也算开了头。王二蛋心里自个画好未来蓝图了,干起活来傻有劲儿。大冬天睡羊圈里的小屋,把自个弄得活像一只腌臜的大绵羊。春天来了,二蛋在地里顶风植棉苗。有人问老板给他多少钱?二蛋说一毛也没给,都在老板娘那儿存着呢。一群人围着他说,‘你还不快点要钱去,以前有三个人上过当,给他家干活没得一分钱,光屁股回家,甩鸡巴吊蛋,一年白干。’王二蛋一听傻眼了,他瞪大眼珠子愣痴大半天,犯了疯牛病似地跑走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