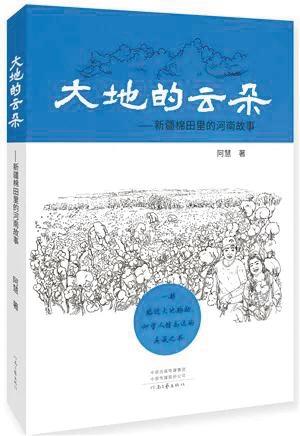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我听着怪紧张,捏笔杆子的手有点抖。任叔说:“这二蛋一猛劲儿跑了十来里,撞开门没见老板影。老板娘一身面粉从灶房出来了。吼他,‘你这二蛋神经啦,把大门撞劈了你赔吗?我看把你当驴肉卖了也不够。’二蛋伸手说,‘给我钱。’那女人一扭屁股进了屋,说,‘钱?啥钱?我没见你的钱。’二蛋跟着她的脚后跟大叫,‘给我钱!我的钱!’老板娘嗷嗷叫,‘你的钱,你哪儿来的钱,我没见你的钱长啥样!谁见了给谁要去。’二蛋圆脑袋红个透,热血往上涌。他从背后箍住老板娘的胳膊,吼,‘你给不给?我只要去年拾棉花的钱,其它的我不要了。给钱我回家!’老板娘拿着刀正在切拉条子,她不耐烦地往后一划拉说,‘滚开!’王二蛋突然感觉右手一阵疼,抬手一看冒血了,右手食指中指都拉中了,一个大口子张着嘴,很快被红血填满了,血珠子成串地往下滴。你说这二蛋能不发疯嘛?他举起血手去夺老板娘的菜刀,那娘们背着身子一晃荡,刀刃子正巧抹过她脖颈,俩人都看见血柱子喷出来,对面白灰墙噗地染红了。老板娘一声不吭地趴到了案板上,小半拉脖子耷拉着。二蛋傻站了半根烟的时间。他拿起刀,冲出院子。地里干活的人,见二蛋跑得像疯牛,半拉身子都是血,手里的刀变成红的了。就在这沟渠边,二蛋正撞见老板扛着个铁锨,慢条斯理地走过来。他嗷嗷叫着冲过去,还喊‘给我钱!’那老板当过兵,一看势头不对,他身子一缩一闪,那二蛋摔了个嘴啃泥,手里的菜刀一家伙飞老远。干活的人瞧见老板用皮带反绑二蛋的手,他一路喊,‘王二蛋杀人啦!他拿刀要杀我。’一群人推推搡搡把王二蛋押送到派出所。”
“我在发庭上最后一次见到王二蛋,他看上去很平静。”任叔说:“当时有个女律师同情他,免费给他当辩护人。可是那二蛋反复说,‘是我杀了老板娘,我想杀了他全家。’科学验证他精神上没毛病,他一口承认杀了人,还要寻老板杀他灭门。”
“哎!”任叔拍拍脑袋说:“有一阵子大家伙儿都议论,说这二蛋小子咋这么傻蛋呢?他只活了二十七年,连女人的边儿也没粘,他咋就那么想死呢?有位专家说了,这跟当事人长期所处的环境有关。王二蛋打记事没见过父母面,他的世界基本是冰冷的。他像一条没有发育完全的草履虫,没有触觉,没有武器,没有安全感。他不爱说话,把自个儿缩在壳里躲藏着。王二蛋到了新疆后,有一阵子心热了,而且一天天热起来,热成一块红铁。可瞬间,一盆冷水泼下来,他的热望滋啦一下灭掉了。被抓后二蛋恐惧万分,他不是怕死而是怕活,怕人心,怕强者,怕活着……”
任叔说:“人家专家说得多,说得深,我也弄不懂。可是后来我还是为二蛋掉泪了,他一拉上刑场,医院的各路救护车,早停在一旁等候了。王二蛋临刑前在遗体捐献书上签了字,他说他的身体没毛病,所有的器官都管拿去用。”
“你不知道闺女,”任叔说:“有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不敢看旁边的病人,害怕看见像二蛋一样憨实的眼睛。真的闺女,你任叔我年轻时读小说读多了,有时也犯神经。”
任叔咧嘴笑一下,我也想咧嘴,但终究没咧动。
晚饭时,任家来了一家三口人,二十多岁的小两口和一个两岁大的男娃子。三口子都胖胖的,一个个健康茁壮的模样。任叔介绍说:“这是我大哥的二娃子一家。”这二娃子挺胸腆肚,一双细长眼,一脸憨厚像。三口子玩了会儿离开了,任叔说,大哥的家在果园前头住,没多远,抬腿就到了。可是我却没有到他家去,任叔说,他的大哥不在家。
三十二朵花
“出家男”任大超
任大超,男,六十五岁,原籍河南周口农村。任二超的大哥,任家的长子,新疆六户地植棉大户。生育两男一女,长子大学毕业,婚后生一女,两年前离婚,剃度出家。二儿子婚后生一子,在六户地种田为业。小女儿嫁在本地。妻子憨傻,任大超一年前出家礼佛。
任叔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红墙金瓦的寺院一角,苍翠柏树的掩映之下,两个身穿僧服的男子并排而立。年轻男子高老者半头,年龄不足三十,光头净额,面色沉静,双目平和。老者六十多岁,花白寸发,额上皱纹叠生,嘴角下垂,双唇半开,欲说还休。
任叔指着照片上的老者说:“这是俺哥任大超,这是俺大侄娃子。”
“两个和尚!”我惊奇地问:“父子俩都出家啦?出了什么事儿?”
“唉,” 任叔坐回沙发说:“这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
“俺哥别看个头没我高,他人聪明啊,打小就是个人精,村里老辈子人说他,‘这超娃子,粘上猴毛就是个猴精啊。’他初中毕业回村务农,对村里的一些人和事看不惯,又性子直,一着急就满口跑火车‘恁这些人都是笨蛋,光知道天天开会,不解决实际问题。’有人训他,‘毛也没扎齐,你能个啥?’俺哥说,‘我就比恁强,恁都不如我!’俺哥有些锋芒太露了,村人有些排挤他,在加上俺爹的问题,俺哥天天烦闷得很。终于有一天,他想不开了,趁大家伙在地里干活时,他转身走开了,一头扎进了机井里。这机井井口小,深得很,干旱时都有半井水。俺哥头朝下扎井里,他说他是真想死。可是,扎下去他就迷糊了,一翻身头朝上,人坐在了井水里,露个头在水面。村里有个老嫂子,扔下锄头去坟堆旁解手,完事了提溜着裤子往回走,见机井旁边半人高的蒿草有人踩过,她好奇地走过去,伸头朝井里看,水面漂着个人头,以为眼花了,又看,妈呀,这不是大超吗?大声喊,‘大超你咋掉井里了?’俺哥闭眼不吭,老嫂子大哭着一路小跑,‘快来人啊!大超掉机井里了!’人都呼啦啦跑去了,喊我大哥的名字,他一声不吭,是缺氧昏迷了。找一个年轻的瘦小伙儿,拦腰系绳子,倒挂着续下去,把绳索缠在俺哥的胳膊下,一群人把他水哒哒地拉上来了。控过水,放在风口,俺哥两个时辰才醒过来。过后,全村人都奇怪,恁小的井他咋翻过身来了哩?恁深的水他咋没沉底哩?俺哥清醒后回忆说,他好像坐在几根粗树干上,枝枝树杈地托着他,让他沉不下去。‘可能是村里捣蛋孩娃投下的。’俺哥这么说。”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