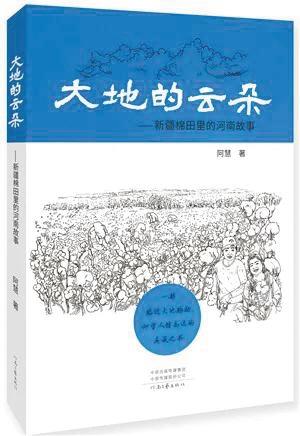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任叔说到这朝相片上的他哥笑了笑,说:“俺哥说‘死不了就不死了,我要好好活,要活出个人样来。’1965年俺哥二十岁,他一猛子扎到新疆来了,跟凫水一样,俺一家子都跟着游过来了。俺哥在这上了户口,接下里想娶个媳妇成个家。他在六户地也有一个中意的人儿。听俺哥说,那女子姓葛,也是打外省迁来的,两条大辫子,一双单眼皮,俊模俏样的。村子离田地远,有时得骑马去干活,俺哥没有马,葛女子就骑着大马找俺哥,说‘你上来吧,骑后边搂住我的腰,搂紧了,被摔着。’到了地了,她想法设法地跟俺哥一个组。生产队用铁犁子除草,葛女子对俺哥说,‘你扶犁我拉马,咱俩一块儿干。’俺哥听出女子的意思了,但他没有表态要娶她,像我当初对朱玉芬的态度一个,他担心葛女子家是地主成分,两个黑五类子女,生下的孩子更黑了,没法走在太阳下。再说,即使他和女子都愿意,葛家的老子也不会同意的,到时候闹掰了,连个村邻都做不成了。”
任叔回忆说:“俺哥那年从新疆回到周口老家,我当时还在县水泥厂上班,只知道他领着一个傻闺女走了,在新疆成亲了,不知道俺嫂子究竟有多傻。后来,我在这安家了,住俺哥的老房子,这才见到俺嫂子。她可不是一般的傻,可以说傻得不透气,跟个实心的擀面杖一样。她生来就傻,又没人教说话。你阿姨认识那傻妮,说傻妮从小到大天天坐门口,不说不笑,鼻涕邋遢,像个泥墩子。俺哥在老家待了俩月,请遍了周边的媒婆,竟没有一个闺女愿意嫁给他。傻妮不会拒绝他,关键是傻妮祖祖辈辈是贫农,傻妮就成了俺嫂子。”
任叔指点着照片说:“其实啊,俺这大侄娃子是老三,前头还有俩闺女,一个是刚生下的当夜,就被傻嫂子的肥身子压死了;一个是半夜喂奶时,俺哥一迷糊没看住,孩子被她傻娘捂死了。多俊的两个小闺女,死时都是小脸儿乌青,鼻孔出血。我这大侄娃子一落地,俺哥就把他搂怀里,日夜搂着,绝不让他挨近俺嫂子。连喂奶时都死盯住,喂饱了赶紧抱走。就这样,大哥的两儿一女才得以成人。”
“老二是女孩。”任叔说:“大哥的三个孩子如今都成家生子了,闺女嫁到本村了,小儿子住在新宅子里。俺哥的希望全都在大儿子身上,当时新疆最好的中学是150团一中,这座中学的教学质量全新疆闻名。大侄娃子初中高中都是在这个学校上的。这娃子沉静稳重,学习也争气,顺利考上了河南大学,在六户地镇响当当的,俺全家别提有多荣耀了。大侄娃子毕业后,与相恋多年的女同学在北京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娃子。大哥从北京看孙女回来说,‘大娃子在公司还是个小头头哩,拿九千多工资呢!’”
任叔搓了搓手掌说:“大哥家的变故,跟那年汶川地震有关。”我从记录本上抬起头,不解地望着他。
任叔面色冷凝,声音低缓地说:“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大侄娃子当时正在佛寺做义务工。闻讯后,他同志愿者们一起,装载救灾物资,连夜赶往汶川灾区。因为电话不通,家人和他失联了。二十多天后,大娃子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他离婚了,剃度出家了。俺哥大惊失色,跑到北京寺院寻儿子。大娃子学习培训去了,俺哥只找见他的一本日记,上面断断续续地写着,‘我们救助一所小学校’……‘惨!惨!惨!’……‘拿什么拯救你啊,我可怜的孩子们!’……一页上贴着照片,大娃子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那孩子满脸是血,衣裳破烂。照片下写着,‘我从瓦砾中扒出来了这女娃,还好,只伤了皮肉。她当教师的妈妈砸死了。这娃不会哭,不说话,除了我她谁也不跟。我们正在想法找寻她爸爸。’;‘在给小学校搭建板房时,同来的好友赵明,被一条毒蛇咬伤了胳膊,高烧不止,只得锯掉右臂……大雨中我仰天长啸,为什么?为什么啊!’在北京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哥没能把大娃子带回家。有一天,我接到大哥的电话,他说,‘二超,我也皈依佛门了。’”
“什么?”我惊讶地说:“他也不要家啦?”
“其实啊,”任叔说,“大哥六年前就离婚了。”
我问:“他有外遇啦?”
任叔沉吟片刻说:“嗯,算是两情相悦吧,我事先也看出了苗头。六年前,我和俺哥一人开一辆新买的大马力拖拉机给人翻地,中午我把带来的馍菜让他吃,他低头掩饰住笑意说,‘有人送。’不大会儿来了个女的,四十来岁,高高大大,皮肤黑亮,骑着一辆黑摩托。她把饭盒塞给俺哥说,‘趁热吃吧。’自个跳上拖拉机驾驶室,突突突地翻地去了,俺哥蹲在地里嘿嘿地笑。我认得这女人,是邻村老蛋的媳妇儿,这老蛋既窝囊又懒惰,大家伙儿都叫他‘懒蛋’,家里地里的活儿都是他媳妇一个人干。女人家再强,这肩膀也软弱啊,我大哥同情她,帮她家打杆、翻地时尽量少收费。俺哥哧哧溜溜、有滋有味地吸着拉面,对我说,‘哥啥也不瞒你,二超,这女人知道好啊,锅里亏了碗里补,天天给我做好吃的。这不,她家的地翻完了,还跑二十多里地给我送饭吃。说实话二超,吃过她做的饭,哥才知道啥叫饭,那傻娘儿们让我吃了几十年的狗食儿啊,二超。’”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