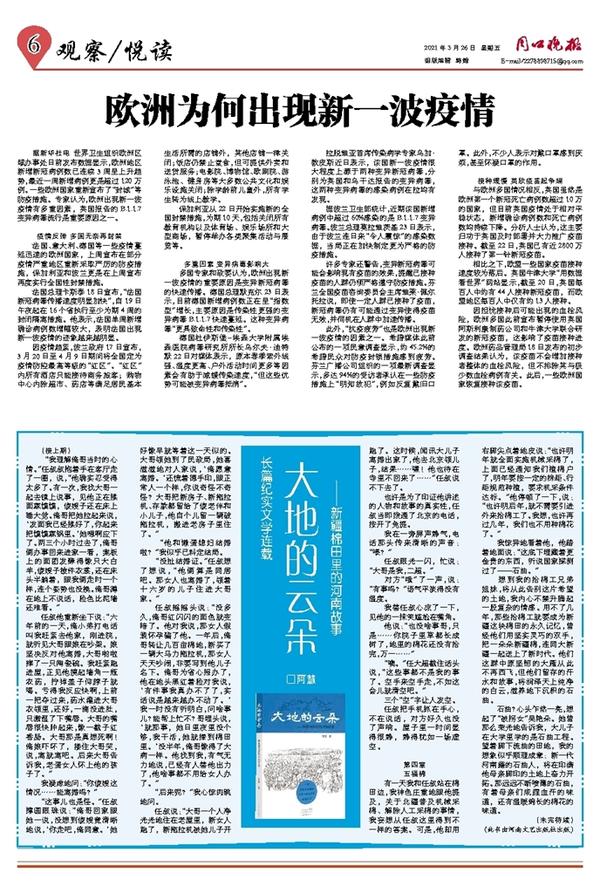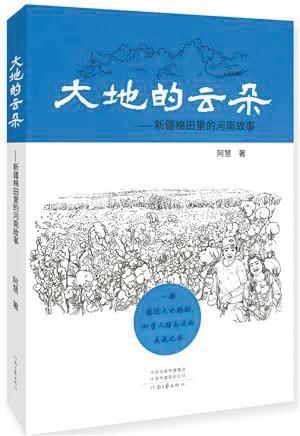(接上期)
“我理解俺哥当时的心情。”任叔叔抱着手在客厅走了一圈,说,“他确实忍受得太多了。有一次,我找大哥一起去镇上说事,见他正在揉面蒸馍馍,傻嫂子还在床上睡大觉。俺哥把她拉起来说,‘发面我已经揉好了,你起来把馍馍蒸锅里。’她嗯啊应下了。两三个小时过去了,俺哥俩办事回来进家一看,案板上的面团发酵得像只大白羊,傻嫂子披件衣裳,还在床头半躺着,跟我俩走时一个样,连个姿势也没换。俺哥蹲在地上不说话,脸色比泥墙还难看。”
任叔他重新坐下说:“六年前的一天,俺小弟打电话叫我赶紧去他家,刚进院,就听见大哥跟娘在吵架。娘坚决反对他离婚,大哥啪啦摔了一只陶瓷碗。我赶紧跑进屋,正见他摸起墙角一瓶农药,拧掉盖子仰脖子就喝。亏得我反应快啊,上前一把夺过来,药水灌进大哥衣领里,还好,一滴没进肚,只溅湿了下嘴唇。大哥的嘴唇很快肿起来,像一截子红香肠。大哥那是真想死啊!俺娘吓坏了,搂住大哥哭,说,离就离吧。后来大哥告诉我,老蛋女人怀上他的孩子了。”
我疑虑地问:“你傻嫂这情况……能离婚吗?”
“这事儿也是怪。”任叔撑圆眼珠说:“俺哥回家跟她一说,没想到傻嫂竟清晰地说,‘你走吧,俺同意。’她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大哥领她到了民政局,她喜滋滋地对人家说,‘俺愿意离婚。’还慌着摁手印,跟正常人一个样,你说奇怪不奇怪?大哥把新房子、新拖拉机、存款都留给了傻老伴和小儿子,他自个儿留一辆破拖拉机,搬进老房子里住了。”
“他和懒蛋媳妇结婚啦?”我似乎已料定结局。
“没扯结婚证。”任叔想了想说,“他俩算是同居吧。那女人也离婚了,领着十六岁的儿子住进大哥家。”
任叔摇摇头说:“没多久,俺哥红闪闪的面色就变暗了。他对我说,那女人假装怀孕骗了他。一年后,俺哥转让几百亩棉地,新买了一辆大马力拖拉机,那女人天天吵闹,非要写到他儿子名下。俺哥为省心照办了,他在地头黑红着脸对我说,‘有件事我真办不了了,实话说是越来越办不动了。’我一时没有听明白,问啥事儿?能帮上忙不?哥埋头说,‘就那事,她日里夜里没个够,我干活,她就撵到棉田里。’没半年,俺哥像得了大病一样。他找到我,有气无力地说,已经有人替他出力了,他啥事都不用给女人办了。”
“后来呢?”我心惊肉跳地问。
任叔说:“大哥一个人净光光地住在老屋里,新女人跑了,新拖拉机被她儿子开跑了。这时候,闻讯大儿子离婚出家了,他去北京领儿子,结果……嘿!他也待在寺里不回来了……”任叔说不下去了。
也许是为了印证他讲述的人物和故事的真实性,任叔当即拨通了北京的电话,按开了免提。
我在一旁屏声静气,电话那头传来清晰的声音:“喂?”
任叔眼光一闪,忙说:“大哥是我,二超。”
对方“哦”了一声,说:“有事吗?”语气平淡得没有温度。
我替任叔心凉了一下,见他的一抹笑尴尬在嘴角。
他说:“也没啥事哥,只是……你院子里草都长成树了,地里的棉花还没有拾完,万一……”
“噢。”任大超截住话头说,“这些事都不是我的事了。空手来空手走,不如这会儿就清空吧。”
三个“空”字让人发空。
任叔把手机抓在手心,不在说话,对方好久也没了声响。屋子里一时间显得很静,静得犹如一场虚空。
第四章
五福棉
有一天我和任叔站在棉田边,我神色庄重地跟他提及,关于北疆普及机械采棉、解除人工采棉的事情,我妄想从任叔这里得到不一样的答案。可是,他却用右脚尖点着地皮说:“也许明年就全面实施机械采棉了,上面已经通知我们植棉户了,明年要按一定的株距、行距规范种植,要求机采条件达标。”他停顿了一下,说:“也许明后年,就不需要引进外来拾棉工了。我想,也许再过几年,我们也不用种棉花了。”
我惊异地看着他,他踏着地面说:“这底下埋藏着更金贵的东西,听说国家探测过了——石油。”
想到我的拾棉工兄弟姐妹,将从此告别这片希望的土地,我内心不禁升腾起一股复杂的情感。用不了几年,那些拾棉工就要成为新疆这块棉田的永久记忆,曾经他们用坚实灵巧的双手,把一朵朵新疆棉,连同大新疆一起送上了新时代。他们这群中原坚韧的大雁从此不再西飞,但他们留存的汗水和故事,将润泽天上纯净的白云,滋养地下沉积的石油。
石油?心头乍然一亮,想起了“被拐女”吴艳朵。她曾那么荣光地告诉我,大儿子在大学里学的是石油工程。望着脚下流油的田地,我的想象似乎顺理成章:新一代河南籍的石油人,将在印满他母亲脚印的土地上奋力开拓。那远远不断喷薄的石油,有着母亲们咸腥血汗的味道,还有温暖绵长的棉花的味道。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阿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