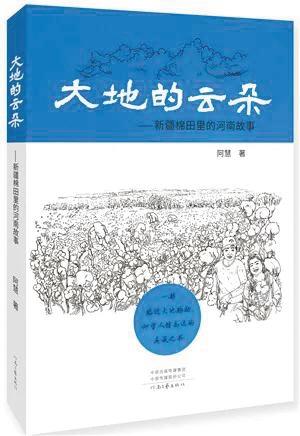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她勉强笑了笑,说:“手里有钱了也不是啥好事儿。我老公转让出去一千亩地,买了房,他和那女的就住一块儿了。”
“你没有去看看吗?”我问。
“没有。”她说,“去了还不打起来啊!打了、闹了有啥用?说不定一闹就过不成了。我和他都不想离婚,那女人有家有口的也不想离婚。我们庄的梦华,跑到广东跟她老公闹,俩人回来就离婚了。她一个人带着个三岁的小妮儿,住在村头老房子里。我看见她就想哭,哭梦华,也是哭自己。那几年,我真是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说句良心话,俺老公跑那么远开荒种地,是想给老婆孩子挣个好日子,他还想在村里给自己挣个面子。在新疆改良土壤时,他在地边搭个小窝棚,一连几个月吃住在里边,有饭就吃,没饭饿着,成天不抬头地干活。”
“唉!”她叹息一声,说,“眼看着地熟了,能种了,他走了。他舍不得走,拉到家后日夜睁着眼,恐怕一闭眼再也睁不开了,见不着他的地了。那天,他吐了半痰盂血,催我说,‘快叫儿子结婚吧,我撑不住了。’”
粉花忍不住哭出了声,她忙掩住口,说:“可怜人。”
杨敏说:“我和公婆连夜商量,把儿子定在明年的婚期,提前到今年的腊月初五。日子太紧,只有五天,儿媳妇孝顺,二话没说,立马回家准备嫁妆去了。婚礼上,小两口给他爸行了大礼,磕了响头。闹洞房的人才散去后,他把俩孩子叫到床头,说,‘过了年,你们就去新疆吧。把地种上,别忘了,拾头茬子棉花时,喊着我,我能听见。’没多大会儿,他睁着眼走了……”
出了杨敏家,我记住了这么一对夫妻的苦痛和不甘,我卷入了他们的秘密和两难。杨敏的老公,那个睁着双眼逝去的壮年人,离开生养的土地,去煨热生存的土地。他以悲壮的姿势,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却终究为了活着而死去。
我长吸一口掺着雪沫的凉气,胸腔一丝隐隐的疼痛。
三、村头的姐妹们
我和粉花刚走到巩庄村头,碰见一群女人,急急慌慌朝这边赶。粉花扬起手臂喊:“你们咋才来啊,晚一步我们就回城了。”
“留守女”汪兰兰说:“我跑了三个村才把她们找齐了。你是没看见,一个个肉哩很,又是抹油,又是擦粉,跟去相亲一个样。”
姐妹们把我围在圈里头,叽叽喳喳乱说话。
“家暴女”江水莲,几乎趴到我脸上看,半天说了句:“老天爷,还真是你!在新疆任老板家的小屋里,你问我这问我那,我以为你是骗子。”
粉花说:“她能骗你啥?你有啥可骗的?”
我摸摸江水莲的歪鼻子,说:“还好吧姐,他没再打你吧?”
江水莲说:“他打不动了,偏瘫了。我婆婆去年冬天也死了,这会儿我当家。”
我说:“翻转得真快啊,你翻身农奴把歌唱,可以打他了。”
她说:“咱不打,他都这样了,看着怪可怜的。”
我掏出围巾分给大家,说:“姐妹们,这围巾里有股棉花味儿,说不定还是你们亲手拾的棉花呢。围上看看,暖和不?”
姐妹们嘻嘻哈哈围起来,一时间,雪白的地头五彩缤纷。江水莲问:“要钱不?”粉花上去踢了她一脚,说:“不要!作家姐送咱的。”
我举起一叠照片喊:“姐妹们,看看上面都是谁?”
“这是啥时候照的?”
“这不是我吗?”
“端着大碗的是我吧?那时候我咋恁能吃哩,一顿饭能吃三大碗。”
“恁瞧瞧,这一地的白棉花喜死个人儿,那时候咋没觉得好看哩?”
“这张拍得好。你看这大棉包,快把我压趴窝了。”
“恁看看这张,作家姐搂着我照哩,她咋没搂你哩?”
“她还跟我睡过哩,咋没跟你睡啊?”
我挥舞围巾阻止说:“停停停!咋扯到床上去了。”
见姐妹们把照片藏起,我知道,这些照片记录着他们在新疆的劳动生活实景,记录着河南拾棉工与新疆棉田的深层关系,记录着中国农业发展时期的一段农民生活史。
我用笨拙的文字把他们记下了,也帮人们和我记住了他们。记住他们的弱小与责任,卑微与高尚,寒冷与热望。记住了他们的泪水、汗水和血的温度。
我问姐妹们还去新疆拾棉花吗?她们说新疆北部全部用机械采棉了,不需要拾棉工了。新疆南部有些地方还在用人工,她们中有人已经转战去了新疆南部棉田。
粉花给我说一段顺口溜:“新疆的钱,不好拿,不是跪着就是爬……”没想到姐妹们都会说,她们一起拍手道:“新疆的钱,不好挣,不是弯腰就撅腚;新疆的红票子,累死河南的半吊子……”说完,她们哈哈大笑。
该是怎样的自信,才能锻造出如此豪放的个性;该有怎样的磊落,才能如此率性吐槽和自黑;该有怎样的坚忍,才能积聚出如此含泪的笑。
2017年秋
“光棍男” 刘欢家
临近安徽地界了,我才找到拾棉工刘欢。之所以这么执着地寻找他,不只是牵念他的日子过得怎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是我在新疆棉田采访的第一位男性。想到他面对我时,那种羞怯、忐忑、纠结和慌张,我便心存不安。三年来,我眼前不断闪现,刘欢讲述中努力想笑却比哭还难看的表情,还有他用力遮掩却又主动撕开被婚姻和爱情刺中的伤口时的窘迫。他对我毫无来由的信任,让我始终无法释然。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