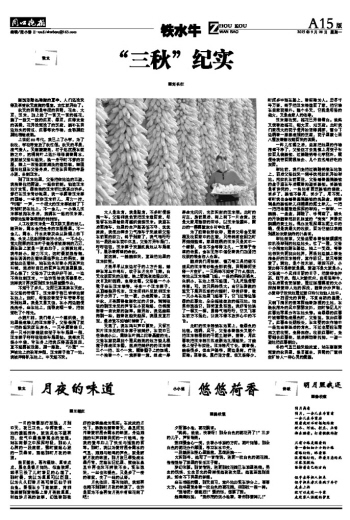散文
刚送走酷热难耐的夏季,人们还没来得及享受秋天凉爽的惬意,农忙就开始了。
秋天的田野是丰硕的田野,花生、大豆、玉米,加上拾了一茬又一茬的棉花,摘了一拨又一拨的红豆、绿豆,红得发紫的高粱,花开没完没了的芝麻,插补在田边地头的南瓜、红薯等农作物,全都脚赶脚地相继成熟。
上世纪80年代,我已上了小学,为了秋收,学校特意放了秋忙假。秋天的早晨,凉气袭人。天刚蒙蒙亮,村子还沉浸在寂静之中,泡桐树叶上还扑嗒嗒滴着露水,我就被父亲叫起来,换一身平时不穿的衣服,蹬上一双亲戚家淘汰的运动鞋,睡眼惺忪地跟在父亲身后,行走在田野的羊肠小道,去掰玉米。
到了玉米地里,父亲把住地边的三垄,我挨着他把两垄,一起往前掰。钻进玉米地才发现,绿油油的玉米秆比我高出许多。穿行在玉米青纱帐里,我一手握着玉米棒的顶端,一手按住玉米秆儿,用力一拧,“咔嚓”一声,一个硕大的玉米棒被掰了下来暂时扔在地上。不一会儿,一小堆儿玉米棒被抛在身后,簇拥在一起的玉米棒,窃窃地说着喜相逢的悄悄话。
人工收获玉米是一项又脏又累的活儿。刚开始,露水会把全身的衣服浸湿。不一会儿,露水、汗水夹着灰尘从脸颊上往下淌,头发上还黏附着些许小虫。一不小心,宽大肥厚的玉米叶子像没有被磨利的刀刃,刷在脸上就是一道血印子,火辣辣地疼。我年龄小,耐力不大,这时候就想偷懒,躲在高高的庄稼林里捉弄地上的蚂蚁,抑或钻出庄稼林,站在地头对着小河高声地叫喊,然后听自己的回声在河道里飘荡,开心极了!父亲为了让我好好干活,一边不停地掰玉米,一边许诺给我买糖果吃,这样我才再次回到玉米地里勉强作业。
不知干了多久,太阳已高高挂在天空。在父亲的带领下,玉米棒子都已乖乖地躺在地上。这时,母亲拉着架子车带着早饭来到地里。我是又累又饿,在小河边随便洗洗手,坐在地上,狼吞虎咽一番,把饭菜吃了个精光。
小憩片刻,我们每人一个编织袋,去地里装成堆儿的玉米棒子。父亲装满了就一把拎起来扛在肩头,一只手握着袋口,另一只手托着袋底往架子车车厢里一倒,玉米棒子呼呼啦啦往车厢里钻。我每次只装小半袋,背在身上把我压得歪歪扭扭,直不起腰板走路,脚一踉跄,“扑通”一声被地上的杂草绊倒,玉米棒子撒了一地。我被摔得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大人是主角,我是配角,不多时便装满一车。父亲和我负责把玉米运回家,母亲留在地里继续用编织袋装玉米。我跟在后面推车,地里的生产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我使出浑身力气推车子来减轻父亲在前面的拉力。终于到家了,我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院中休息,父亲打开车厢门,呼呼啦啦,玉米棒子欢蹦乱跳地从车厢滚下,展示着辉煌的金秋。
就这样,一趟趟往来,直至把地里的玉米拉完。
月亮早早从东边村子的上方升起,蟋蟀在草丛中鸣叫,蚊子在月光中飞舞。白天收获回来的庄稼,晚上要熬夜拾掇出来,次日及时晾晒,免得发霉。父亲搬一个小凳子坐在玉米堆旁,手拿一个玉米棒子,从顶端撕开包衣,玉米须和外皮就和玉米棒子分开了,一软一硬,分成两堆。正值中秋,月亮圆得像刚吃过的月饼。刺刺啦啦的剥玉米皮的声音在小院响起,仿佛演奏着一曲农家的旋律。刚开始,我还能坚持剥一些,随着夜越来越深,我眼皮直打架,最后竟不知啥时睡着了。
天亮了,我在鸡叫声中醒来,只留三四片玉米皮的玉米棒子被辫好,在院中已经堆成小山,露珠在叶瓣上闪着晶莹的光。父亲在庭院里找个通风敞亮的地方栽几根檩子搭成玉米棚,然后把辫好的的玉米辫三个一把、五个一簇,顺着棚子上的粗绳,一个挨着一个,一簇挤着一簇,组成一串串金光闪闪、光芒四射的玉米攒。此时的村庄,房前屋后、树上树下一片金黄。这是大家用勤劳的双手,以玉米做颜料,画出的一幅幅豫东乡村丰收图。
为了赶着秋耕秋种,通常父母会无暇顾及收回家中的庄稼,只待稍有空闲之时再细细整理。家里晾晒的玉米只是其中一个缩影,但也不会等得太久,一贯善于偷盗的老鼠,会在无形中催促着我们加紧把收获的粮食存入仓库。
随后我们用铁锹、镰刀等工具把密不透风的玉米青纱帐全部砍倒,田野瞬间变得一片空旷。一只蚂蚱不知受了什么惊扰,突地从玉米秸里飞起。一般的蚂蚱灰褐色,体积小,在地上很不起眼,飞几尺远便要停落。可,这只蚂蚱很大。当它在澄澈的蓝天下展开五彩的内翅时,非常好看,像一只小鸟在地里飞起落下。它飞过旁边碧绿的红薯地、朵朵棉桃绽放的棉花地。如果你想捉它,那简直是妄想。我好奇地追了一程又一程,累得气喘吁吁,它又飞落在前方不远处,让我不得不放弃心中的不甘。
此时的玉米秸铺在地面上,像绿色的地毯。晾晒、风干,父亲拿着榔头又逐个把玉米秸根部的干泥土敲碎,接着,用红薯秧把玉米秸三五成群地扎捆起来,才能装上架子车拉走。玉米秸尺寸长,横着装,能装很多,但生产路窄,两边是树,行走困难;竖着装,虽行走方便,但又装得少,时间多半耗在路上,着实难为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玉米秸运回了家,把它堆在自家院墙外。整个冬天,它既是母亲的柴火,又是全家人的依靠。
玉米刚收完,棉花已开得雪白。爸妈又慌着拾棉花、割大豆、刈芝麻。此时我们家很大的院子便开始变得拥挤,窗台下边晒着一排排成捆的芝麻,院子里横七竖八摆放着刚收割回来的高粱。
一阵儿忙碌之后,总算把地里的作物清理干净了,父亲这才去集镇上用架子车拉回几袋碳铵、过磷酸钙等化学肥料,顺便给我带回两根油条、几个煎包等好吃的东西。
犁地前,我们先把过磷酸钙撒在地表上,而后父亲找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开始犁地。拖拉机在前面走,父亲端着盛满碳铵的盆子跟在车后顺着沟垄丢碳铵。丢碳铵是有讲究的,一块地有固定碳铵的袋数,丢多了,碳铵不够用,丢少了,用不完。有时我也会端着盛满碳铵的洗脸盆,闻着刺鼻的碳铵味儿和潮湿的泥土味儿,一把一把把希望撒进深深的犁沟。一犁犁、一趟趟、一盆盆,脚酸了、手臂麻了,额头的汗珠随着拖拉机粗重的“突突”声滑向新翻的黄土地。偶尔发现深埋在泥土中的蛹,便是我最大的收获,因为它能让我闻到原始农家烧烤的扑鼻香。
犁地结束,父亲总要拿着铁锹掘掘拖拉机没犁到的地边地头。忙了一通,父亲十分满意地蹲在路边,抽上一支烟,等着地邻来共同找出地界,再沿地边插上事先准备好的玉米秸秆,算作标记,就只等耩麦了。耩地,是个技术活,掌控不好,小麦出得不是稀就是稠,麦垄不是大就是小。父亲挑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把麦种先拌药,晾干后,倒入木耧兜内,由母亲牵牛,他在后面负责摇耧,通过摇摆幅度的大小控制着麦种入地的深浅,随着沙沙声响,小麦种子欢快地通过耧口均匀地钻入地中。
一扫而光的田野,不复当初的盛景,只剩下满目的衰草围绕着赤裸的土地,在晚秋清冷的风中瑟瑟发抖,这时惟见几片红薯地零星分布在地头旁。当绿绿的红薯叶被寒霜染成黑色时,父亲说,该出红薯了。红薯生长期较长,在主要的农作物中一般充当着垫后的角色,不过也要赶在霜冻之前收完,免得冻伤。收获红薯时,先要割去红薯秧,然后挥动着抓钩,一垄一垄地把红薯刨出。
冬的气息已越来越浓重,站在刚刚耩完麦的秋田里,极目望去,田野的广袤和空旷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