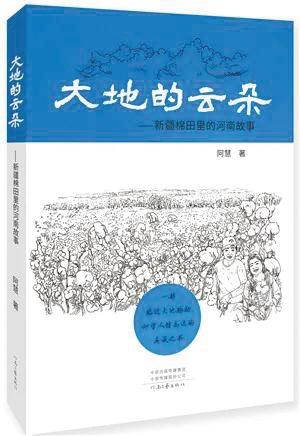(接上期)
十五朵花
“上门男”白路根
白路根,男,三十五岁,原籍湖南耒阳,入赘周口。妻子河南周口人,儿子两岁,妻子刚怀第二胎。
这又是一朵为数不多的雄花,他见我走来,就主动取下口罩礼貌地微笑。可是,还有一个口罩长在他脸上,一块四方白印,一笑一动。白印以外的眼睛,下巴,脖子,耳朵都是黑红色。这是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身材瘦长,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初见他,就让我想起南方的竹子。他操着南方口音说:“我在湖南出生,现在住在河南岳母家,做了上门女婿。”
我说:“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很长的爱情故事。”他笑得很幸福。
他说:“白路根这个名字,是我爸爸找人按风水、笔画给起的,我一直在考虑这名字的含义。爸爸五十岁那年有的我,妈妈当时四十八岁。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十八岁。我爸妈都是军人,身体都不怎么好。据听说,喝满月酒时,一个战友叔叔说,‘你们俩身体都这样,又生这么个小孩,这不是害人家吗?
“果然,我刚满周岁,妈妈就心脏病复发去世了,我还没过两岁生日爸爸也走了,我记忆里没有父母的印象。当时,爸爸的战友要领养我,姑妈不同意,她说,我是她哥哥唯一的根,也是他们白家的根。我就跟姑妈在广州生活,十二岁被姐姐接回湖南,报了户口,上到中专毕业,学的是普通车床专业。后来到深圳恒泰制衣厂打工,在那里认识了我老婆陈唤唤,我比她大七岁。
“2003年,我和陈唤唤分到一个组,都是搞喷漆,那年她只有十六岁。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女孩,只是默默干活,很少说话。陈唤唤却很活泼,爱说爱笑,经常在我跟前蹦来跳去,打打闹闹,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个小孩子,人长得也好看。时间长了,我俩有了感情,知道她家住河南周口,家里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
“她家里人不同意和我谈恋爱,说年龄相差太大,其实是嫌我没有父母,没有根基,怕她受苦,就把她叫回家了。一年没回来,也没有书信,但我相信,我俩的感情没断。后来,唤唤去广东东莞打工,离深圳很近。那一天,我坐车去东莞找她,她来深圳找我,我们在街口会了面,我俩都哭了。那一年,我俩一有时间就来回跑着,相互看望。2005年,我把唤唤弄到深圳打工,租房子住在了一起。那年唤唤十八岁。
“2006年,我想多学技术多挣钱,就带着唤唤离开深圳到厦门,做了电镀工,唤唤在一家工厂做手机配件。快过春节时,唤唤怀孕了,我往河南打电话、写信,希望能征得家人同意,让我俩结婚,可是得来的都是坏消息。
“我和唤唤只好去医院,把孩子做掉。那个春节,我俩是哭着度过的。
“那一阵子我心情很复杂,很痛苦。也理解唤唤父母的做法,谁不想让自己的小孩过得好呢。我就向唤唤提出分手,不想在害这女孩,跟着我没有什么幸福日子过,劝她放弃我。可是唤唤不同意,天天跟在我身后,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受苦受累跟着你。
“我从心底感觉很甜蜜。这中间,唤唤回过一次家,她妈妈电话里说家里有急事。唤唤一上火车,我就想她这次真的回不来了,但心里认定她一定能回来。两个月后,唤唤出现在我面前,她只带了点路费就跑回来了,身份证被她妈妈扣在家里了,那时买车票还不是实名制。唤唤是被家人拉去相亲的,说定了亲就去打结婚证。唤唤偷跑出来,回到我身边。我心里又喜又忧,知道女孩子得罪家人的严重后果。
“2009年的一天,家里又来电话催唤唤回去,这次是让我送他们的女儿一起回,说是娘家人要看看我,我一下子感觉有希望了。
“家里人热情地招待了我,虽然晚上让我俩分开睡,但我心里已经很知足。
“唤唤的父亲找我谈了话,说既然打不散,你们就成了吧。给唤唤补了身份证,又开了户籍证明,把我俩送上公交车。一上车唤唤就哭了,那一刻,我也流泪了。”
白路根声音堵在喉咙里,我也鼻子酸酸的。我说:“你们俩真是不容易。”
稳定一下情绪,白路根继续说:“2010年,我带着唤唤回湖南领了结婚证,在父亲的老家耒阳举办婚事。父母只留下两间破房子,我俩在那里拜了天地。没有亲戚朋友到场,族人也没来几个,他们都出去打工了,搬到城里住了。只有一个堂哥帮我忙活,看上去他也很冷淡。
“我领着媳妇来到父母坟地,我俩把坟上的杂草清理掉,跪在那儿烧纸,倒酒,心里难过,止不住流泪。我只见过父母在部队时的照片,不记得父母的模样。我说,‘爸妈,我是你们的儿子路根,这是你们的儿媳妇陈唤唤,我们俩结婚了,给父母敬酒了。请二老保佑我们在外健健康康,没钱慢慢来。保佑我俩相亲相爱,不离不弃……’唤唤哭成一个泪人。
“我们在镇上宾馆开了间房,在那里度过了新婚之夜。我俩回到城里继续打工,工作虽辛苦,但感觉很幸福。没过多久,我老婆就怀孕了。姐姐有心照顾我老婆,让我们回来和她一起住,一起经营她的小饭店。可是饭店生意不景气,我只好又出去打工,老婆刚生完小孩,带孩子很辛苦。这时丈母娘打电话来,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就回来吧。
“2013年6月,我们一家回到河南周口。唤唤带孩子在家,我去厦门上班,还干电镀活,每月三四千。但我肠胃不太好,吃饭少,没力气。 今年6月回来了,在家帮亲戚搞装修,没有活儿,挣不来钱,老婆又怀了第二胎,想要个女孩,做B超还是男孩,男孩就男孩吧,白家又多了一条根。但是负担更重了,我还是想挣钱,就来新疆拾棉花。老婆不让来,担心我身体吃不消,我说,先找个地方赚一点钱吧,赚一点是一点。”
白路根始终微笑着向我讲述,他在讲述中品味爱情带来的甜蜜,对于拥有这份纯真爱情的他,苦难的童年算不了什么,苦累的生活也算不了什么。
他说:“我老婆勇气可嘉,她明明知道,嫁给我生活的路会很难走,但她还是历经八年的坎坷选择了我。她在经济上支持我,在精神上鼓励我,再苦再难也不放弃我,不放弃这份感情。我心里感觉过意不去,娶了她就像害了她一样,没有给她一个好日子,一个好的家。
“儿子的户口,本想在湖南老家落户,但想到老家那里没有亲人照顾,河南这里有父母,亲人多,老婆孩子不孤单,就落户河南了,把根留在这里。
“我一直在考虑父亲给起这个名字的含义,孩子户口落下了,我才明白过来,父亲是让我,无论根扎在哪儿,都要走好脚下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我把白路根的话,飞快地记录到本子上,他说:“大姐,我和老婆要个理想。”
我抬头问他什么理想,他说:“想在周口开家湖南湘菜馆,在姐姐饭店帮忙时,我学会了几道招牌菜。今年给丈母娘过生日时,我操刀露了一手,大家都说怪好吃。”
我说:“我也想尝尝,可惜你的饭店不清真。”
我俩正说笑,白路根的手机响了,他一看号就笑,背过头去说话:“嗯,挺好的,天天吃白米,不累……”
我知趣地走开,手机里飘出一个女孩子的声音,细细的,柔柔的,纯纯的,似一缕轻柔的暖风。我忽然感觉到了春天,棉田里吹来一股爱情的风。
耳边想起冰心先生的那句话:“有了爱就有一切。”
做晚饭时,月清嫂在蒸馍馍的大锅里,专门给白路根蒸了一碗大米饭。这个未来的湘菜大厨,为这碗白米饭思念了四十多天。
吃过饭,姐妹们各自进行短暂的休整,舀热水洗头洗脚,暗影里清洗下身。没有专门的洗浴间,洗浴间就是大院子。零下气候,泼水成冰,刚洗完头发,跑旱厕解个手,回来就像顶了一头细钢丝。洗好的衣服,搭在绳子上,不大会儿,就硬成了一张干羊皮,风一摇,咔咔地响。
我就着风洗了脸和脚,在没冻上之前往屋里跑。一双绣花鞋横在我眼前,绣花女莫鲜灵笑嘻嘻地说:“姐,别嫌弃,这双鞋送给你。”
我接过来,把绣花鞋从右手转到左手上,问:“给我的?为什么?”她说:“看你喜欢就送你了呗。”
走到门口她又说:“俺婆婆说了,喜欢的东西要送给喜欢的人。”
啊,我还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低着头,我喜眯眯地进了屋。
坐在沙发上我端详这双鞋,仍是黑底黑帮黑襻子,但鞋头却绣着一朵大菊花,花瓣开得如张开的手掌,每一片花瓣的颜色都不一样。那柔长的丝线,描上柔长的菊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片花瓣,七种色彩,似开在黑色天幕上的七彩烟花。那炸裂般的美艳,蕴含了绣花人浓郁醇厚的情感。
姐妹们入睡可真快,头一挨枕头就呼呼上了,这枕头是世界上最厉害地催眠器。
好像刚把被窝暖热,好像刚有了一个梦的开头,门外有人硬着声音喊:“起来啦!吃饭啦!”床铺上开始有人翻身,揉眼,哼唧,发脾气,放小屁儿。昨晚,张立老板就安排要早睡早起,说是杨老板的哪块地离村子比较远。可是没想到要起这么早,我看看手机,还不到五点钟,确实有点早。有人边提裤子边骂娘,含含糊糊,不知道骂的是谁的娘。有人说要回家,今天就走,一定得走。
吃了饭,提上包,水杯里灌上水,爬上两辆咚咚叫的大半截头车,就没人说话了。寒冷封住了每个人的嘴,留些热气在肚里,连下边的口都要招呼得紧紧的,不能随便乱跑气。
车灯一打,寒气像受了惊吓,一团团地乱飞,飞不远,绕着光柱转。
柏油路冻得硬邦邦的,车轮子碾去,哒哒哒,一车人蹦跶个不停。
随着颠簸的节奏,有人哼哼了两声,那呻吟,是那种真实的疼,像惊动了肚子里的胎儿。我拿眼去寻摸,一堆女人挤成一团,你靠着我的肩,我抵着她的背,把脑袋埋在避风处,分不清谁是谁。低头想,这两天吃住在一起,没听说谁怀孕呢?怀孕事小,颠流产事大。正一个人瞎操心,抬眼见,车灯的光柱里晃入一条人腿,正疑惑,一晃又三条腿,再看是两个人的背影,厚棉袄,军大衣,围巾包着头,辨不出男女,胳膊窝夹着编织袋,双手插进袖筒里,踢踢踏踏沿着路边走。前头又有三个人,相似的打扮,听见后面有车响,纷纷回头望,六个眼珠闪烁成六个亮幽幽的白点,样子看起来有些诡异。我吓了一跳,曾被夜间蓝幽幽的猫眼吓到过,没想到,人眼也那么可怖。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