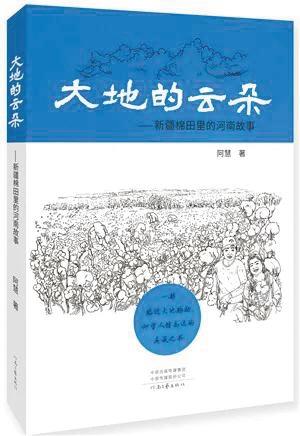□阿慧
(接上期)
突然间车窗外一片黄亮,我探头一看,熟透了的小麦,完美承继了黄土地的基因。河南这片温热的黄土地,产生出全国十分之一以上的粮食,四分之一以上的小麦,以沉甸甸的国家担当,为14亿人扛稳了粮食的安全重任。
麦田边黄白的土路上,邓大哥扛着把铁锨站在那,仅半年多的时间,他的头发又白了不少。大哥看到我时,眼睛一眯,又一亮,说:“真是你哩,快去家里吧。”
邓大哥的家在村西南,我们穿村而过时,见水泥路两旁,整齐排列着一座座砖瓦房,一家一院,偶见一两栋白墙红瓦的小楼,看上去像短衣衫的人群里走出个长袍先生。各家的院落有大有小,大门楼却一律又高又阔,估计能开进去一辆农用四轮车。
一棵上了年纪的大槐树下,几个妇女坐在砖块上说话,几个找不到砖块坐的,就顺手揪掉一只鞋,一屁股坐在鞋面上,亮白着一只脚在那里比划。我们快要走近时,女人们突然静音了,有的背过脸不看我们,有的仰着脸盯着我们看。没等邓大哥开口介绍,我就笑着说:“老姊妹们好啊!待这儿凉快着呢?”
女人们明显愣了一下,很快笑着说:“是哩!是哩!来了呗?”
光着一只脚的女人麻利地站起来,捡起屁股下的鞋子,弯腰穿上鞋,而后说:“上俺家喝口茶吧?”
我拉着她的手,说:“不啦不啦,谢谢妹子啊,回头去你家喝茶。”
开车的朋友从驾驶室偏过脑袋,眼睛里满是惊叹。
邓大哥把铁锨从右肩换到左肩上,对我说:“城里坐办公室的人都大样,你跟人家不一样。在新疆拾棉花那会儿,大家伙儿都看出来了,你跟我肩膀头子一般高,眼睛鼻孔不朝上。看得起我们农民,不嫌农村人脏。”
我说:“哪里话呀大哥,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泥巴妞,刚出门没几天,总不能不认识家里人了吧。”
一直以来,“自然,真心,不造作,不矫情”是我采写拾棉工时的真实姿态。在北疆农六师四场八连的棉田里,初次找见我们周口拾棉工时,我浅薄地显现出自己的小优势,煞有介事地又是拍照,又是录音,使顶着骄阳劳作的他们相当反感。一个姐妹生气地把脑袋埋进棉花棵里,说:“别照我!”我暗自脸红了一阵子,把相机扔到田垄上,默不作声地帮她拾了一天棉花。晚上还死乞白赖地挤上她的床铺。一天天过去,使我自然地融入拾棉工的生活,活像找见了在别处生活的家人。我帮50多位老乡拾过棉花,也一天天地把他们的日子拾到了。我拾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命运,他们深层的灵魂。也一天天地找见了自己,那个原本真实柔软的我。我告诫自己:“你真了,文字才能真,才能显见那些隐蔽的真心与真相。”
进了邓大哥的高门楼,见院子里停放一辆四轮车,车斗里放着镰刀、麻袋、绳索、簸箕、扫帚,看上去满满登登。大哥把扛着的铁锨放进车斗,说:“这些都是收麦子用的,明后天就开镰。”我熟识这些农具,有种久违的亲切。想起小时候曾亲自割过麦子,还亲自使用过它们,不禁泛起一丝苦甘。
那时候,割麦、打麦都是人工,麦忙时大人小孩都使上。工人放工,学生放假,就连不沾亲带故的城里干部,都脱下皮鞋,挽起裤腿,下到麦田里干活。那种火热的灵动,庄重的仪式感,凝滞在我童年的记忆中。
我问邓大哥:“现在收麦不是用收割机了吗?这些老物件用不着了吧。”
邓大哥说:“规整的大块地,机器收割起来方便些,沟沿、地边,边边角角的小块地,还得用镰刀一把把割下来。”
我问他今年种了多少麦子?他说,28亩。不光是他的地,还有两个儿子的,就连邻居家撂荒不种的地,他也捡来种了。
我说:“没想到大哥你不光会拾棉花,还会拾地呢。”
他说:“刚才咱从村里过,你都看见了吧,一半的人家锁着门。人都进城了,剩下些走不掉的妇女老人守着村,老人干不动农活儿,田地就租给别人种了。前几年逢到麦季子,在外的人还回来收收麦、种种秋,你瞧瞧现在,没回来几个人。”
“你那两个儿子也不回来收麦吗?”
邓大哥学着大儿子的口气说:“爸,你叫我回去弄啥?一斤麦子才卖一块多钱,除去种子、农药、化肥、浇水、除草花的钱,能挣几个钱啊?你想想啊爸,我们两口子加上我弟弟两口子,四个人回去的路费得花几千块,请假回家工钱又扣几千块。这还不算,弄不好还得丢工作,我在外边磕头拜门的,好不容易找个稳当点儿的活儿,收了麦回去又不稳当了,弄不好还被人顶替了。爸,你算算这个账,我回家割麦划算吗?你别急,我在网上约了一家收割机,连夜割,说好了,到时候我用支付宝把收麦的钱转给他,你不用管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